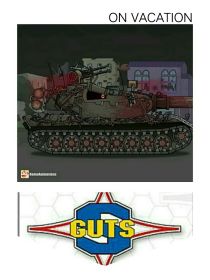第九十六章 于谨
胡三帮我上好了药,现下仍替我打抱不平:“她倒是愧疚了,你可是受了罪,你看看你这胳膊,都五天了,还肿这么高。”
“没什么。”
我摇摇头掩上胳膊处斑驳的伤痕,心下没怎么在意,继续忙着我的公务。
身侧只好安静下来,默默替我整理起了文书。
前日的那场意外现在回想起来都让人……尴尬。
妇人吵架也会动手动脚,而我家母亲大人激动起来尤甚。
谁料到我好生生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两世为人从未那般狼狈:被一妇人推下半人高的台,一股脑栽进花丛,胳膊扎了满胳膊的刺儿,想想都让人郁闷。
而追究罪魁祸首,却是两根年久失修的旧栏杆。
当然还有我那因为闯了祸,心虚得再不敢吱声的母亲。
我蹙眉覆住被蔷薇花刺伤,肿了整整五日都没怎么消下去的胳膊,除过得一个“以后离发怒的女人远些”的教训,总而言之还是十分庆幸的。
还好伤的是不常用的右胳膊,不然家务事闹得人尽皆知不说,若因此耽误朝政大事,便让我这个新上任的大冢宰太没脸面了。
人活一口气,脸面为最大,人死了,也得死得有尊严。
宇文护被诛,朝廷照旧给了他体面的丧礼;此事压了下来,那些个人精自然猜得其中内情,眼见既成事实,只好心照不宣地闭口不提;此前布置在太师府里的十二军换了下去,未生得半分乱子。
而如今我做我的大冢宰,五弟做我的辅助,半月以来接手的诸事务已渐渐步入正轨,一切在变,一切又似乎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我思索间胡三已挪到我跟前。
他安安静静地瞅了我半晌,唉叹一声。
像是失去了什么珍贵的东西,颇为落寞地拉着我的袖嘀咕道:“祢罗突,我最近看着您越发老成,都不见从前的样子了。”
孝伯也曾有如此孩子气的时候。
可他只比我小一岁,如今也有十七了。
上辈子的事没办法与他道明,我只作温和一笑。
“我自然不能是以前的自己,不然如何处置大事呢?胡三,你是我的亲信,日后府里内外事务繁多,我都需要你的帮助,我交代你的事务你也应当学着一些,你明白了吗?”
胡三小鸡啄米地点着脑袋个不停:“……哦,哦,明白了,我都明白。”
我正与胡三叮咛着话,外头却报于谨来了。
李弼、赵贵、独孤信等人或被杀或过世,侯莫陈崇、贺兰祥年老,眼下唯剩于谨和宇文贵等人还能支持,我近来也正是得了他们几位的扶助,方使得朝野些微的动荡稳固下来。
我之所以敢除宇文护,便是因为这些都在我的计算之内。
当然他们也很满意我,近来与我在国事上有所交流,皆道我心机深厚,智力非凡,且若是上位不仅不会听皇帝的,皇帝还得听我的,比那位连番对皇帝动手,行迹已然有些可疑的宇文护更为好用些。
好虽好,我这人却唯有一个缺点——
“殿下勤劳清俭,严于律己,这些都是好事,”我待搀扶着他入了座,却被笑眯眯地拉住胳膊:“只是为政须缓而宽,就如对待自己一样,过度地苛刻只会造成身心的耗竭,这是君子修养的中庸之道,也是治国处事之道,明白吗?”
听这人话里话外的意思,想必是我那皇帝大兄派来的吧?
我肿着的胳膊被他拉住不得动,只好咬咬后槽牙应承下来:“伯父说得是,我回头就改。”
此人曾经劝我放下一切修养身体,我当年心里有恨,只表面上敷衍了过去,后来亲政之后昼夜操持事务,果然只六年便没了命。
“圣人也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谦和就坐,垂目不软不硬地顶撞道:“我之欲,是富国强军,圣明长存,我之不欲,乃是声色犬马,贪淫奢侈,我将我所欲施予人,不欲者不施人,想必是圣人要求的君子的德行,不知伯父以为如何?”
我俩大眼瞪小眼许久,谁也不让谁。
照旧是对方先败下阵来。
“你呀!”
于伯父哭笑不得地指了指我,又发觉这般指我似乎不大礼貌,于是真切赔了两三句罪,而后自顾捋须沉思,不知在打算什么。
“殿下有扶立宗周之志,我等莫敢不从,富国强军亦是吾等之志,”于伯父那乌溜的眼珠转过一圈,忽对我深意一笑:“至于圣明长存么——”
于伯父说得对。
我可是清楚地知道某些人的打算,圣明长不长存无所谓,他们要的“圣明”,在于那个维护他们利益的大冢宰。
我心下有数,是以故作肃穆地对西宫拱了拱手:“周公之例在前,圣主仁厚宽和,成康之治又有何难?新朝初始,万事因遵法度,四时有序,万物有时,神明与人分隔,天子与臣的区分,当从这里开始。”
我如此作答,于伯父满意了,遂只与我再叮咛了几句便告辞而去。
我送着他出了府邸的大门,又目送他上车离去,外头天阴欲雨,后背已不觉汗湿。
罢,我也只是为了保住我那个大兄,至于后人,我只能尽力而为,若实在不行,那便只剩了“杀”字一诀。
杀人,不到万不得已,我并不欲启用此道。
即便是我那个最为讨厌的六弟。
风大了些,雨也大了些,空气里的潮腥略过鼻尖,天上的雷声轰隆隆滚过,一道道送走张狂而无节制的夏。
(双男主)白莲花养成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超级胜利队与坦克们:阻止金翅雕(续)
- 简介:小号的第一季后续的故事,本作阿尔法小队将会改名米尔内小队,但小队三位成员的名字不变,本作中关于坦克的角色是home坦动的,并且这个系列可以算是坦动+小花仙+喜灰+和平以及MC等其他系列的大杂烩同人作【PS:本作出现的人物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
- 35.6万字2年前
- 穿越水浒当好汉
- 简介:黄飞,一介学生,因酷爱水浒,崇拜梁山好汉,终口里脑海被水浒、梁山、晁盖、武松等将的满满的,机缘巧合,一次恶梦醒来,竞发现自己在水迫梁山,还随身自己崇拜的好汉身上,从此一段奇幻之旅开始了………
- 52.0万字2年前
- 少年特战队第六季
- 简介:少年特战队后续,本人不是正宗军迷,若有不对请指出开学每周更四篇
- 4.0万字2年前
- 三国之超级霸主
- 简介:穿越到东汉末年,逐鹿中原,争霸天下!本书数字版权由“智阅”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联系话本客服(我的-设置-客服咨询内)。
- 27.0万字2年前
- 三国:黄初之年雨落时
- 简介:【本文已于2021.8.16签约完成】【更新较慢,但一定不会放弃,可放心食用】标题出处:黄初八年正月雨——曹植《慰情赋》他是枭雄曹操最为宠爱的四子,名唤曹植,文采斐然。曾在铜雀之上作《登台赋》一首,也曾立志尽己所能报效国家,更是赋诗言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而他是曹操存活下来的长子,名为曹丕,更是曹植最尊重的长兄。六岁会射箭,八岁知骑射。却在十岁那年亲眼目睹昔日敬重的兄长曹昂为掩护他而死。曹丕:子建…我最大的愿望,便是你不要步为兄的后尘曹植:现在连二哥都不愿信我么?
- 12.2万字2年前
- 不一样的帝国
- 简介:如果有什么写错的地方,请大家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毕竟作者不是万能的,我也是很喜欢写小说,请大家多多包涵。
- 6.3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