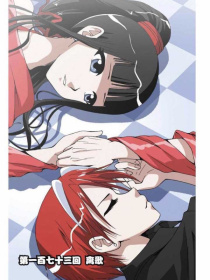第二十五孩子妈妈害了你
第二十五孩子妈妈害了你
七十九
自郑泽宇去到香香香大馅饺子馆打工。唐润杨也在他打工的饺子馆附近的聚福源当了名切菜工。
几乎与郑泽宇的饺子馆同时下班的聚福源,已经九半点了,还是灯火辉煌,虽然零星地散落着几桌客人,但服务生们还是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在那些穿着红衣蓝裤的女服务生中,郑泽宇一眼就看见了唐润杨。
看到很乡巴的装束也掩饰不住唐润杨的美丽,郑泽宇更感到自己是个罪人。然而他今天看到的唐润杨不是笑脸地向他奔来,她正痛苦地站在吧台前。
“我简单给你包扎一下,还是快点去前面的诊所,口子太大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在老板娘的埋怨声中,郑泽宇看到唐润杨左手的食指被白色的纱布缠裹,正有殷红的血滴滴嗒嗒地渗落。
“去诊所,快,怎么这么不小心。”一知晓唐润杨的手被切了,郑泽宇立即拽着唐润杨去找诊所处理伤口。太晚了,几家诊所都关门了,好在有一家社区医院的门诊仍照常营业。
“得逢针。这么漂亮的丫头,会留下伤疤的,多可惜啊。”负责处理伤口的护士惋惜地说。唐润杨只是抿嘴笑。这一笑,笑得郑泽宇心如钝刀子割般的难受。只有郑泽宇知道,为了能和他的饺子馆近些,唐润杨硬是应聘了聚福源切菜工的伙计。想想这段时间里,唐润杨经历着比自己还要强烈的身心煎熬,郑泽宇更难过得要窒息了。那关于唐润杨拯救陪伴自己的一幕幕又过电影般地跑了出来。
于是郑泽宇就决定不把被扣罚工资的事情告知唐润杨。他要学着做个有承担的男子汉。
“郝全被抓了!”那天晚上,唐润杨早早地来到香香香饺子馆门口等候郑泽宇。一见郑泽宇就慌张地喊。原来在家休息的唐润杨在今晚的滨城六十分上看到:今天滨城市公安局捣毁一贩毒团伙。当画面切换到几个被抓人的脸时,唐润杨惊得跳起来。被抓的三个男子中,竟然有一个是郝全。怎么办?他能不能把郑泽宇曾经答应过要帮他卖冰的事情抖落出来?警察能不能因为郑泽宇曾是郝全的好朋友而传讯郑泽宇?一想到事情的严重,唐润杨竟吓得哭了。她要尽快地告知郑泽宇,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这个消息对郑泽宇无疑于宇宙毁灭的毁灭,世界末日的末日。
“我们还是到他的家里看看吧。”沉默了许久,郑泽宇终于开口。
“去看他妈妈?”
“是的,去看他妈妈。”唐润杨很想听郑泽宇说说为什么要在这个关口去看郝全的妈妈。但郑泽宇的沉默,让唐润杨不敢多问,凭着对郑泽宇的了解,唐润杨知道,这个时候,除了执行他的决定,什么都苍白的。
顾不得唐润杨的疑问,顾不得饺子馆的老板说人手不够不能给假。第二天一大早,郑泽宇和唐润杨坐上了快轨,直奔郝全在滨城丽景小区的家。
八十
郝全的家在89楼的1-2,前年的这个时候,郝全曾带自己来吃过饭,他的妈妈给他们做了她最拿手的手扒羊肉。这一切多像一场梦。
看起来一定有警察来过。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说是发大财,原来是这样来的?”
“生养了这样一个儿子真是造孽。”
“干什么不好?干这害人的事情。”
“都是惯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肯出力,就干这等畜牲的营生。”
“他妈妈可怜,守了这么一个儿子,真是不幸。”
“命真是苦到家了,好容易拉扯大了儿子,竟是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
…………
围观人们的议论,听得郑泽宇心里异常地悲戚。他只想快快地见到郝全那可怜的妈妈。在他最恨自己母亲的时候,是那么地敬仰这个母亲。因为这个母亲是那么地娇宠着自己的爱儿,除了赞美,从不指责爱儿所做的一切,把工资的四分之三都给了儿子花,她看儿子的眼睛永远都是在欢笑着的。儿子,有一点的闪失就会要了她的性命。记得她不止一次说过,郝全到123中读书的第一个月,她每天都会跑到路口倾听去往北新市火车的鸣叫,然后追着火车跑很远很远的路,边跑边喊着爱儿的名字,深夜也会如此。那个时候郑泽宇多么希望自己有这么一位母亲啊。为此,他甚至叫她为干妈。现在,爱儿被抓,要走上不归路,这位母亲将如何地承受啊。所以郑泽宇在得知郝全被抓,第一个想到的是要看望他的妈妈。
“你来了吗……你是郑泽宇吧……郝全的事情你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救他……你不是他的好朋友吗……你走吧……不要你来看笑话……”没等郑泽宇开口,躺在床上的郝全妈妈一看到郑泽宇就要起来,她要赶郑泽宇走。
“阿姨……我也是才知道……”郑泽宇的辩解起了作用,郝全的妈妈不再赶他走了,而是盯着他的脸看。直直的目光看得郑泽宇慌慌的。没想到两年不见,郝全的妈妈仿佛老了二十岁还多。她的方脸已经成了倒三角的锥子型了。眼神僵直,空洞,若不是她还能发出沙哑的声音,你绝对不会想到她还活着。
“他就是不听啊,虽然他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他那些钱不是好来的,我苦口婆心地劝,他就是不听啊。我天天都在担惊受怕,只要一听到警车响,我就心跳得站不住了.我天天都向菩萨祈祷,祈求佛保佑他,祈祷这天不要来,可是还是来了,自作孽不可活啊。”郝全的妈妈说着就去扯自己的头发,打自己的脑袋,可是没有气力的她只能揪着小绺头发干嚎,她流不出眼泪了,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她没有气力了,她的气力已经耗尽了。她只是干亮着眼睛盯着爱儿的方向本能机械地哭嚎。
“干妈,干妈……”面对这个精气神完全为悲伤掏空的母亲,郑泽宇找不到任何安慰的字眼,哪怕是一个音节。他只能在心里说,郝全,世界上最爱你的妈妈被你杀死了啊。
“别关……大权会回来的,他有时候也喜欢走窗户。”可能是苍天也为一个可怜的母亲垂泪了,突然的一片乌云掠过,十二月的北方天,飘起了零星的雪花,那个看护郝全妈妈的自称是郝全三姨的女子,要去关门,关窗户。刚才还只是游丝气力的郝妈妈,腾得从床上站起来大喊着,郑泽宇和唐润杨刚要告诉她郝全不会回来了,被三姨制止了,她流着泪对郝全的妈妈说:“不关,我们不关,大权会回来的,你会把大权盼回来,等回来的。”
“是的,他会回来的,我刚才还梦见他跟我说,他后悔每次都让我一个人过节,让我天天都盼他到深夜,他说,他不上网了,好好的,做个乖的孩子。”郝全的妈妈又揪着自己的头发傻笑起来。在她的傻笑中,唐润杨失声长哭,陪伴她的三姨失声长哭,门外,窗户前围观的人群很多的男女都在呜呜地哭。
郑泽宇的人在这哭泣声里晕眩了。他的眼前不时地叠现着妈妈肖迎春愤怒的,哭泣的脸,耳畔一会儿响着妈妈的‘儿子,你什么时候能不让我再一辆辆地数着车辆等你啊。’“你什么时候能不去网吧正常回家啊。”一会儿响着韩剑锋老师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呢,你选择的道路是死路啊。“对不起,错了,对不起,太错了。”他抓住了眼前这个可怜母亲的手喃喃地说着,他给她跪了下来。
“你别跪,地上凉,你没有错,大全,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听妈妈的话,以后咱好好地读书,咱不和哪些王八蛋在一起。”没想到,郝全的妈妈把郑泽宇当成了郝全,爬到他的面前,从头到脸就开始抚摸。摸着摸着就大哭:“大全,是妈妈害了你啊,如果妈妈不是什么都依着你,坏蛋就害不了你了……”
“阿姨,阿姨,我是泽宇,我是你的干儿子郑泽宇啊。”在郑泽宇和三姨一阵呼唤中,郝全的母亲又清醒些,清醒的她就拉着郑泽宇的手,有气无力地说:“你是个好孩子啊,你妈妈有福气啊,可是,我救不了大全了。我太娇惯他了。我害了他了。”又一阵干嚎中,郝全的妈妈再次地晕厥过去。在一阵慌乱中,大家掐她的人中,啃她的脚后跟,她又缓缓地醒过来。一醒过来,又“我的儿啊,我的大权啊,你回来啊”地叫。
“你们还是回去吧,你们哭,她会更难过,现在我们都做不了什么。”郝全的妈妈稍微平静下来时,三姨说,,郑泽宇也觉得现在的情形,自己在这里也是不合适的,只能悲愤地和郝全的妈妈说了再见。出来的时候,他很想问问什么人:郝全是不是一定会判死刑。但是没人可问。那些围在门口的人们已经散去。郑泽宇只能默默地走着,一路上,他忍不住去想和郝全在一起的一切,想着郝全妈妈以前的笑脸和爽朗的笑声,想着想着他的泪就一串一串地流淌。
“我要是被抓,我的妈妈怕也是活不了的,她也是一个人拉扯我,只是她不想惯我怪毛病,只是她太想让我为她争气,出人头地……”回到家里,倒在床上的郑泽宇低声地对唐润杨说,干涩的眼睛盯着天花板。郝全的被抓和他妈妈的悲怆让他崩溃了。
“你的妈妈曾经就像郝全的妈妈拉着你的手那样拉着我的手,说她要救你,说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堕落。你们只想着你们自己痛快,没想到身边人的感受,尤其是妈妈的感受。”唐润杨说着又一抖抖地哭,她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和姥姥姥爷了。
这夜,唐润杨走后,郑泽宇几乎在雪地里站了一夜,哭泣了一夜。凌晨的时候,郑泽宇开始发着很厉害的高烧,他却没有打电话给唐润杨。
等到第二天晚上,唐润杨来看他的时候,郑泽宇已经烧到了四十二度了。人也在半昏迷中。唐润杨冒着风雪把郑泽宇背到了附近的诊所。
“怎么才来啊?”诊所值班的是个年近六十的男大夫,他量了体温,又听了郑泽宇的前后胸,说有杂音,怕是烧成了肺积水或者是急性胸膜炎,要他们赶紧到大医院去。
“风雪太大了,明天再去吧。”望着窗户外更猛烈的飞雪,郑泽宇还在搪塞。唐润杨知道他是怕花钱,他们的身上实在没有太多的钱。
“不行,就是下刀子也得去。”在唐润杨的坚持下,郑泽宇带着身上仅有的四百元,在滚滚的风涛和雪浪中,跟着唐润杨去到了滨城市民一向认为最好的医学院。
八十一
“四十五度。”
“肺部有水泡。有阴影。”
“急性大叶性肺炎,伴随右胸胸膜炎,住院。”
检查的结果吓坏了唐润杨。人懵懵地瘫着。
“医生,我们不知道这么严重,我们没带那么多的钱,明天上午补可以吗?”当知道住院必须得交三千元押金,唐润杨恳求地说。问过他们住址后,医生答应了,但还是加上了句:“必须明天上午前交,我们医院不是慈善机构,”
在要给姥姥和姥爷拨求救电话的瞬间,顿了顿,唐润杨却拨通了肖迎春的手机号码。
“阿姨,我是唐润杨,我和郑泽宇在医学院,郑泽宇发着很厉害的高烧,烧成了大叶肺炎和胸膜炎,得住院,需要三千元押金……”
“我马上过去。”不等唐润杨说完,肖迎春就沙哑着声音说。一会儿,她又接到了肖迎春的电话:“丫头别慌,我马上过去。告诉郑泽宇有妈妈在,什么都别害怕。”太好了!是时候了!这个电话几乎让唐润杨兴奋得跳起来,可当她面对窗外升腾得乌云般密集的大雪时,心被抑郁塞满了。
怎么下这么大的雪啊。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雪啊。视线里除了些浓雾般的气团在翻滚,蒸腾。什么都是模糊的,混沌的。仿佛置身在一个蛮荒的世界。路灯,霓虹灯的光芒都被这雪缠裹住了,昔日璀璨的光芒被稀疏成毛毛虫模样,只好不服输地放射着孱弱的光斑。借助这微弱的光斑,你看到的房屋,汽车,楼舍,市街都被一片莽莽的白严实实地裹压。远处马路上,一撮撮的行人,正在推着深埋在雪里的车子,一群群的环卫工人正拼命地挥舞着雪铲,或紧跟着铲雪车向马路上洒着溶雪剂……
“雪太大了,阿姨怎么过来啊……”望着眼前的雪雾,唐润杨一筹莫展。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不仅不见肖迎春的人,也没有电话来,打过几次也无人接听。慌急得唐润杨满走廊里踱步。此刻,她更担心的是肖迎春的安全。
而郑泽宇的高烧仍然不见退,一会儿四十多度,一会儿三十九度。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可是唐润杨还是怕啊。看得出来,自去见了郝全的妈妈,郑泽宇就盼望妈妈肖迎春能来到身边。当唐润杨要把医生要他住院的消息告诉妈妈时,他没有如往常般强烈地阻拦。他不知道外面的雪下得如此地大,虽然烧得说话的气力也无,但还会时不时地问唐润杨几点了。唐润杨清楚他不是问时间,他是在盼妈妈。直到医生给他打了镇定针剂,才肯睡去。
已经凌晨三点半了,依然不见肖迎春的身影,疲惫不堪的唐润杨,决定在郑泽宇的身边打个顿。可刚刚一闭上眼睛,就被一阵逼人的寒气袭击得一个机灵地站起来。
天!!!眼前的一幕惊得唐润杨钢水浇铸般地动弹不得。怀捧着保温瓶的肖迎春出现在唐润杨眼前!以为是幻觉。定定眼睛知道不是幻觉后。唐润杨泪如雨下。
凌晨三点四十零六分钟,汗流浃背的肖迎春来到了医院,来到了郑泽宇的病房,出现在盼望她的唐润杨面前。
运动鞋是湿的,膝盖以下的长裤是湿的,黑色的羽绒棉袄也被白雪浸湿,前胸和双肩是厚厚的一层白,像披挂着一袭大白披风。那是雪水和汗水冻在一起的杰作。
“阿姨,你怎么来的?”
“怎么样?还烧吗?医生怎么说?钱我带来了。”肖迎春没有回答唐润杨的疑问,直奔到郑泽宇的床前,边询问,边用嘴唇贴着熟睡的郑泽宇的额头。“还烧,他的耳朵发红了,病很重。他小时候就有个毛病,一耳朵发红,就是在高烧,就要闹大病,只要一看见他耳朵要红,我赶紧抱着他往医院跑。”
“已经说好了,先住上院,明天办理住院手续。阿姨,不着急,你歇会儿吧。”
“不,我得赶快和护士要点酒精和棉球,他烧到三十八度时,就应当用棉球搓他的手心,脚心,额头,和前胸,他小时候就这样,我经常给他搓,我得去告诉医生,总打退烧针不好。”
“阿姨,你歇着,我去告诉医生。”跨向门外时,肖迎春打了一个趔趄,险些栽倒。唐润杨扶住了她。这个时候值班的护士走进来:“三床的家属来了,这么大的雪怎么来的,能开车吗?”护士看到有人在这个大暴雪的天气里,凌晨来到医院,吃惊不小。
“不通车,我是走着过来的。”
“家在哪里,近吗?”女护士瞪大眼,她注意到了肖迎春挂着厚厚冰雪的双肩。
“从秀月的小龙街走过来的。”
“天啊。那是从东头到西头,十多里,就这么走过来的?!”
“是,从夜里十点走的,雪太大,不好走,不然三个点就到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赶明你病了,你儿子能为你这么走吗?”女护士感慨着,转向了唐润杨说:“多好的妈啊,可要好好孝敬。”
一听到肖迎春是走着来的,唐润杨的人彻底地呆住了。很久以后,只要一想着一个矮小的母亲在暴风雪里,在夜幕下,怀捧着为儿子熬的米粥,毅然决然地走了十几里地,为的能早些地守候在儿子的身边,而这个儿子曾经是那么地淘气,动手打过她,把她心爱的首饰偷着卖掉……唐润杨的眼睛就潮湿了。
就是要整治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青春与离歌
- 简介:“你是否也曾答应过为她遮风挡雨不让她受一丝委屈,直到生老病死也绝不离去,为她一颦一笑恍然惊起,对她爱,舍不得别离”-后来你们终于分开,她是否存在于你遥远的记忆里,偶尔想起,心痛不已?多年了,她早已不在身边,不在眼前,却在这里。
- 1.2万字2年前
- 千金小姐的复仇
- 简介:一位善良大方的女孩一直被她的妹妹讨厌,就在这时她突然反击,她的计划会成功吗?那就开始阅读吧!
- 0.3万字2年前
- 搞笑子
- 0.8万字2年前
- 恋魂缠(新改)!
- 简介:标题已被作者吃了!
- 0.3万字2年前
- 我的美女总裁老婆.
- 简介:该简介已被管理员屏蔽
- 2.0万字1年前
- 大海深处的秘密
- 简介:美人鱼和普通人类
- 0.3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