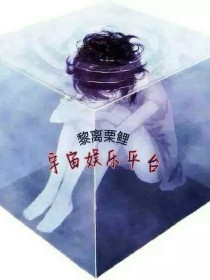无题
小序:忆昔民国二十五年,12月12日,西安,华清寒夜兵谏,文思索索,故作此篇。
他嗓子吊了一腔又一腔,功也练得差不多,闲来无事,于是寻了处有老阳儿的地方,靠着藤椅消磨时间。他不得不感叹洋人的会享受﹣﹣这是栋洋楼,二楼特意留出个没遮拦的小阳台,大抵是作下午茶用。
但洋楼主人根本没有用下午茶的习惯,于是这阳台便闲置下来,正巧让他逮了空子,拉来条藤椅,眯着眼睛曝老阳儿。
他抬眼瞧去,目光所至皆是清一色的洋建筑,被日光晒得刺眼。他心中忽地生出悲悯﹣﹣他从未见过如此光景。站在景山的最高处,极目也只能看见清冷的胡同口。一并许久没人住的破旧四合院,或许晴好时能看见这里,但也只是影影绰绰的一抹,掩在烟华中。他深知,自己不属于这冷峻的大理石建筑,他生是画栋雕梁的人,死是榫卯梁椽的鬼。
大抵只有这里的几枝白梅能略带给他些慰罐丁。黑风过,白海上的雾被吹散,让鼻尖萦绕上一缕花香。扑面而来的暖意提醒他,春已经来了。
他起身,想再唱支曲儿,但他常唱的那儿出,自己早已腻了。新花焉用旧曲?他自嘲。思来想去只余一出《牡丹亭》,他不大唱。昆乱场面不同,科班规矩严,师父教了他又不让他唱,实在扫兴。好容易唱了一回,还没唱罢就被送来这里。既得空儿,索性唱个尽兴。
唱曲要吊嗓子、他于是改换闺门旦的做态,摊着兰花指、绕个腕花:"雨香云片,才到梦儿边。无奈高堂,唤醒纱窗睡不便。泼新鲜冷汗粘煎,闪的奴心悠步亸,意软鬟偏。不争多费尽神情,坐起谁忺?则待去眠。""不好,须得做了妆色。"他戏瘾上来时不管上下尊卑,竟支使洋楼主人拿胭脂来上妆。后者倒也顺从,找出闲置许久的胭脂给他用。他也不嫌弃胭脂落灰蒙尘,软笔过处,鬓边眼梢流露逦迤风流。即使粉墨头面与洋楼格格不人,只要是在如此妙人脸上,不管是否合适,便觉得清丽可人,是这人间不该有的尤物了。
一折《游园》下来,他戏瘾过足,倚着藤椅阖眸小憩。洋楼主人知他脾性,也不打扰,只是将白梅发的嫩枝折下来,簪在他鬓边,于是这梦有了白梅香气。
便是入梦了。
香梦沉鼾,他恍惚间寻得一处临水小亭、亭前隐隐是洋楼主人招手。他迎上去。后者捧了头面戏衣、要他换上。他不肯、这等文采辉煌的戏衣,休说他,就连给太后唱过戏的祖师爷也不曾穿过。"你领情便是,不用管科班规矩。那些俗套最可厌,外人面前不得已,这会子休再怄我。"洋楼主人再三地央他。
后者无法,只得换上,拿硬话村洋楼主人:"我本是好意,少不得提防点,怕走了大折儿而已。"洋楼主人含笑夔立,拿过戏单,点了出《惊梦》。
……
“为什么选择唱戏啊?”
“我只是想唱出中国,唱出我眼中的盛世华夏。”
“戏曲,是我毕生所念,唱之一字,为中华之绝响。
爱与罪语言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all喜:喜你到底在哪
- 简介:因为妹妹的遗忘,最后把喜儿搞丢了
- 2.3万字2年前
- 宇宙娱乐平台
- 简介:一个从宇宙各个星球或不同时间点上随机抽人,集中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空间里,通过战斗、升级赢得生存时间……大学生李容桃在她以为会安静的毕业时被“不幸”的抽中了……但,谁知道这也是宇宙娱乐平台的不幸呢
- 3.4万字2年前
- 她从地府来
- 简介:《异事簿》分散到各地,所到之处,民不聊生。我奉命将其回收,还请各位乖乖配合。
- 2.5万字2年前
- 溟渎杂货铺
- 简介:你……内心中有渴望什么东西吗?爱情?财富?呵,来到这里都可以给你。只不过……你要付出点代价啊…(本小说感情线缓慢,莫要着急)
- 1.7万字2年前
- 我穿成作死捉鬼主播
- 简介:言檀没有想到她这么倒霉,先是看小说看起劲通宵猝死,然后意外穿进小说里面,没有想到居然穿成了她忍不住口吐芬芳的一个作死捉鬼女主播,天杀的啊……
- 0.5万字1年前
- 异鬼百楼
- 简介:23世纪,人们一直在追求刺激……“嘘,在门后,有人敲门……门前,是谁呀?”……“你看啊,人心难测啊,那门前会不会是你呢?”异鬼啊,真的存在……它们,就在你的身旁路过游戏不能退出哦~你猜,谁是怪物?
- 0.7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