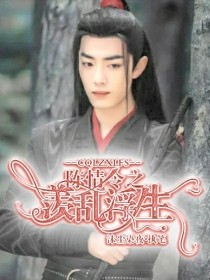鬼蛊 (三十四)颠覆
三月是去拜祭的,但她没带任何祭品。张起灵当时在门口对着阳光检查一个拓本,见三月出来,目光短暂地凝在了她身上一会儿,没说什么,但是站了起来,意思是要和他们一块去。
时间过去太久了,三月去看她娘时早没有悲伤,顶多是因为物是人非生出些感慨。她娘在她的描述中是一个无论何时都要体面的人,所以长大后,三月总会细心打扮后再去见她。
她娘葬在郊外的溪谷。那确实是个很漂亮的地方,不论冬夏总有花开,虽荒无人烟,但没有一丝衰败的感觉。
那种自然带来的美感会让人自内而外的感到放松。特别是对土夫子来说,草地,阳光,本就美好得无与伦比。
墓的具体位置已经找不到了。黑瞎子曾问过三月,当年为什么没给她娘立个碑。当时她的回答,还颇让人感触。
她说这是族里的传统,巫族人下葬后不立碑。
“我们生于天地,死了,埋在土里,就回去了。有了墓碑,逝去的人就是那个碑而已。没有墓碑,没有任何东西表示这个人曾经存在过,那这世上的一花一草,一滴雨水,一阵风,都是他。”
是啊。人生一世,何必一定要留下什么。
无墓可扫,所以说是拜祭,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只不过是在这儿待一会儿。三人并排躺在草地上,阳光晒得人太舒服了,张起灵不一会儿就开始闭目养神,黑瞎子有一句没一句的扯着皮,三月偶尔接两句话。
但没多一会儿,聊天声会越来越少。最后,四周都安静下来了,没有人睡着,但也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躺着,感受这难得的宁静。
有时候三月会在这个时候,悄悄侧过头去看黑瞎子的侧脸。因为从那个视角看,能隐约看见他墨镜下的眼睛,虽然他闭着眼,但看着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心绪会在这个时候飘散开。
她长大了,而他依旧年轻,毫无变化。这么多年的平安是黑瞎子和张起灵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换来的,她心里清楚。从把她抱回来起,身旁这个永远不着调的男人给了她一个新的人生。
也许是目光太过浓郁,黑瞎子总会发现,但又先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称她毫无防备,不轻不重弹她的脑门一下。由于她在走神,每次都会被这一招吓到倒抽冷气。
奸计得逞的黑瞎子会笑得格外猖狂,没皮没脸的来一句:
“黑爷我丰神俊朗的,不能白给你看那么久,今天晚上得加菜。”
每年都会有这么几天,不大的溪谷里迎来三个人,日落后,满目桃花又在风中飘摇,望着他们离开。
之后的几年,三月又跟着两人下了不少斗,经验攒了不少,绝对已经算个出色的土夫子了。可是,“狐仙显灵”再也没有出现过。
三月一度怀疑自己的危险雷达失灵了,但事实上,那几年黑瞎子和张起灵确实没有遇到过大的危险,发生的事情都在掌控范围内。
那段时间无可赘述,日子一天天过着,一日三餐,暮鼓晨钟,没有任何波澜。但正是这样,才让人感觉更加心慌,好像头顶悬了把菜刀,却又迟迟不掉下来。
这是什么行当?脑袋挂在裤腰上走路,这么久不出事,本身就是怪事。好像一切的平静都在预示着,有什么无法估量的事将要来临。
果然,平安顺遂这个词,就不是他们能够奢望的。
当时是三月初,几人都记得很清楚。因为三月生在三月十四,那时正好离她的十九岁生辰很近。
从清晨开始,当天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变数,没有任何危险来临的预兆。
可到了正午的时候,黑瞎子上一秒还在乐不可支的给三月讲着道上的一个八卦,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了,之后直挺挺的晕倒在地,肢体触地,发出“咚”的一声响。他个子太高,一倒下,像座山崩塌了一样。
黑瞎子会晕倒,这事完全不在三月能反应过来的范围,一下子懵了,而离他更近些的张起灵闪电般冲了过去,托住他的头免得他摔伤要害。
可是,张起灵刚过去不到半秒钟,突然整个人晃了晃,按着心脏,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双腿一软,总算撑着没晕过去,只是单膝跪地,手撑着地,一皱眉头,随后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血液的红色在地上蔓延开,不远处的三月,怔怔地看着那过于扎眼的颜色。
她从小到大的观念里,都觉得这两个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所以眼见着他们同时倒下,于她来说和天塌了无异,她一时间根本不能接受,足足在原地僵住了三秒。
但幸好她不是遇事就会被吓懵的人,当即给了自己一巴掌让自己冷静下来,冲过去先扶住了张起灵,后者则对她摆了摆手,又指了指黑瞎子,示意她先去看他。三月扶着张起灵在地上坐下,颤抖着手去试黑瞎子的脉搏。
他的嘴角也溢出血,没有了知觉,前后不到一分钟,他的脉搏竟然已经有了减弱的迹象。三月立刻准备给他作心肺复苏,手刚按上他心口,又觉得不对,闭上眼睛,用尽全力调动自己的特殊感官,仔细感受,却发现他没有中蛊。
可是,这明明就是中了烈蛊的症状。
另一边的张起灵已经是在靠意志强撑着了,突然,他好像是看到了什么,睁大了眼睛,却没有力气再说话,扯了扯三月的衣服,手指向院子外面。
三月顺着他指的方向转过头,却看见了大约二十多个穿着一样白衣的人,正齐刷刷的以一种阴冷到怨毒的眼神盯着他们,一步步朝他们走来,像是刚从地狱里爬出。
盗笔衍生:鬼蛊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龙宝来袭:娘亲嫁不嫁
- 简介:【本文已签约,请勿转载】【原创女主cp润玉,文明阅读,本文无脑宠人物严重ooc,较真者/高洁者/讨厌者/对此种小说有洁癖者勿进紧急避雷此类文,创作属个人乐趣,文笔拙劣,不喜者左上角出门即可,已明确标签,现知道还看让自己不适者与耳无关,不感兴趣就别看那是在自找虐!】片段一:林兮忆看着她生出来的大小不一两颗蛋,呃……这是她生的,内心崩溃,某天比较大的蛋破壳而出,从里面探出一个粉嫩粉嫩的小脸蛋,冲着她奶声奶气喊“娘亲~”。片段二:林兮忆看着眼前皎皎如天上明月,朗朗如林间清风的白衣男子,知道他是小奶娃的爹爹后,林兮忆忍着不舍一颗蛋蛋递给他,然后抱紧粉粉嫩嫩小奶娃“小的给你,这个我要”。
- 15.0万字2年前
- 天道循环
- 简介:禁止任何形式的搬运转载——【2022-06-22完结落笔】天道震怒,重来一回,又是怎么样的光景?【2022-08-25完结落笔】番外一:魏婴重生,只为自己而活,又是怎样的一般情景?【2023-02-24完结落笔】番外二:蓝忘机重生,又该如何改变这一切?【连载中】番外三:蓝启仁梦醒,看着周围的一切,他又会如何?
- 28.7万字2年前
- 延禧攻略之错爱.
- 简介:乾隆:“朕还真是喜欢你这样的坏女人”长夏:“傅恒我不能爱你珍重”傅恒:“阿夏,我明白你的苦衷,下辈子你等我好不好啊我真的好累”富察容音:“小夏,你不能再有回头路了”阿宁:“主子,你这又是何苦”本文和历史没有任何关系,原著党请不要打开阅读,请勿上身真人。
- 0.5万字2年前
- 乱世佳人第二部之重获新生
- 简介:这篇文章主要是围绕着重阳与莲心;王恩与娜娜;子谦与淑琴;康远与秋月他们四对在电视剧最后结尾的时候经历了生死离别的考验,还有经历了因战乱不得不分离的场景。但最终在我写的这篇续集里重获新生;凯旋而归并且重逢在一起。另外我还要把这部剧里的两对单身男女:贺天与小蝶;杜康与美馨都写到一起。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以及他们这六对在之后的日子里幸福美满,但是他们才过了两年的平静的生活,就迎来了国共两党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三对男主与女主在商量之后决定暂时离开上海。在路上这个大家庭里的几对夫妻与子女走散。走散之后,他们有的回到老家,有的去往别的城市一边过着分散之后的生活,一边找寻着亲人。直到十三年后的某一天,曾经走散的大家庭里的家人因子女的关系,团聚在了一起。团聚之后,他们继续过着幸福的日子。而他们的子女也在这平静、安宁的世界里生活,上学,以及找到心爱之人。之后他们的子女与心爱之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 6.0万字2年前
- 陈情令之羡乱浮生
- 简介:假如在穷奇道死的是魏无羡,假如金子轩没有死,师姐没有死,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拆忘羡cp“我魏无羡想杀谁,谁能阻拦?谁又敢阻拦?”他掐住了他的脖子,眼睛通红嗜血!“你敢杀她?那么就用全天下陪葬吧!”
- 3.1万字2年前
- 长月烬明:我来拯救小魔神
- 简介:拯救小魔神。一睁眼,满目璀璨。正是此行的目的地——大夏皇室。处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叶小将军,什么时候回宫了?”耳畔一句轻吟,清冽中透着一丝玩味,还有一丝诱惑。这是回眸一看。
- 63.1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