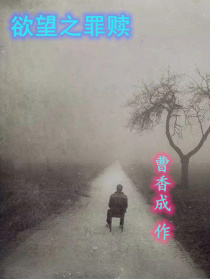五
访草
我很少访人,却常访草。朋友们都有职业,各忙各的,而草则永远安详地在那儿,我自己便像一株草,总在家里,朋友们来,很少找不到。
这个世界若没有了草,人便无法活下去。一个地方若望不见草,对于我就成了牢狱。此时我活在草种多到让我有选择的地方,就像食品多到让我只选取佳肴珍馐的筵席一般,故我感到十分幸福——虽然对于我自身以外的世界我感到十分不幸。
我的围墙门,就像陶渊明说的“门虽设而常关”,门闩经常蒙着一层锈,偶尔开门时,就沾满了手:有客来时,到村子里去买吃食时,上城市买书时,出去访草时。
单是庭面上便有三四十种草,其中如碎米知风草、小画眉草、线叶飘忽草,便可爱得有如小天使,有如天真稚气的小女孩。有了这些草,我实在可以不必再去拉动那生了锈的门闩到田野去。可是一如家里虽有几橱架的书,时而忍不住还是要出去买几本,这庭面边的草就好像是我的另一橱架的书,每日阅读着、摩挲着,给了我无上的快乐与安慰,然而既已知道外边还有些橱架上没有的,就忍不住要出去。
有时正看着书,书页上忽照出一片明丽的阳光,一排石决明鲜黄色的花,像一群黄蝴蝶在阳光下闪烁着,于是我便拉动了那生锈的门闩出去了。
日历撕到了九月一日,大溪床上整大片雪白的菅花开始展现出台湾无可比拟的季节美。这九月的初旬中旬,我出去欢迓,下旬我出去惜别。
有时我在没有车辆来往的大阡陌间漫步好几公里,为的是要长时间从夹道两旁无尽延展前去的草获得绵绵不断感到的温馨。
红毛草庭面就有,白茅庭下也有,一时渴念起那大景观的粉红和白,我也会禁不住出去。
看见大片蓝天有一块映绿,那底下或许是一片新装的草原,于是我也出去。
在田畔路旁蹲下去跟草说话,是我最大的愉快。
各个角落有各个角落的草。有时我不出门,就在屋角边访草,或者反过来说,草到家来访我了。一连下过一二十日的雨之后,那大树底下的屋基或后墙上,就不期然有一片新绿吸引住我的目光,藓苔和小冷水花不知几时来家了。
萧、艾、蒿是草原三姊妹。艾、蒿庭下就有,萧则已随着童少年时光一起消失,于是它成了我的童少年时代的象征,每怀念起童少年时光就想起萧,怀念起萧就想起童少年时光。那一年我在近山脚的荒地上发现了一小群落,仿佛见着童少年时光返转。不久再去,已杳无踪迹。一个小学生在那里放羊,问我何所寻?我说寻萧。小学生笑着说:搬家了。我问:搬哪里去了?小学生说:搬到无人的地方去了。的确,这个时代有人的地方万物就不好存活。最近我在绝对无人到的山脚溪床沙地上发现了一大片。啊,但愿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有人到,好让我的童少年时光跟萧草群落一起常驻!
十一月起,小金英(兔儿菜)遍地是,随着朝日的升起,满田野绽开千千万万朵黄金也似的小花,灿烂的闪烁着千千万万点的金光,仿佛大地随着季节来到,那土层中含蕴着的金质就凝聚着开成了花,要来增饰南台湾美丽的冬春二季一般。这个季节一到,我就频频拉动围墙门的门闩,门闩再不生锈了——而且雨季也过去了。小金英随着日出展蕊,直开到晌午便一齐闭合萎谢,第二天晨光开了它又随着而开。这半年花期的田野,上下午截然是两样世界。下午在田野间走着,会觉得上午直似幻境。但是这一两年来遭村人当药材无保留地采拔,景观已经衰残。
春天一到,满路满阡陌原是到处黄蝴蝶,一忽儿停在草尖上,一忽儿飞起,千点万点,明明灭灭,起起落落,停下时是蝴蝶花,飞起时是花蝴蝶——我一直将它看成世上唯一会飞会舞的花,是异常珍贵的景观,却也已随着童少年时光消逝了。今年初,我在一处已枯的豆田看见了约五十只的小景观,谛视良久,看到惨淡而且褪了色的童少年时光,不由感到一阵凄然。
村人每个人都记得全村人的名字,在村道上遇见,不单是点点头或挥挥手,而且还唤名。田野里的草,对于我,就跟村里人一样,在路旁田畔遇见,我总要唤唤它的名字;有的,我甚至会站在一旁告诉它说:“你晓得吗?你有许多名字,也唤这个,也唤那个。”比如萧,也叫香蒿,又叫青蒿,又叫茵陈蒿,台湾农人还叫蚊子香——农家大量用它来为牛熏蚊,使得萧很快趋于绝灭;而现在农村没有牛了,萧看着可能复苏了。
英国伟大散文家乔治吉辛喜欢遇见不认识的植物,借着书本的帮助,下一次看见它在路旁闪耀时叫出它的名字。能够叫出原是不认识的草名固然快乐,但熟悉的草,唤着它熟悉的名字更加亲切。
我不是食草的动物,但我没有草便跟食草动物一样活不下去。我固然喜爱孤独,但若不是天上有千万点星星,地上有亿兆根青草,我一刻也无法孤独下去。其实我有这么多的伴,我并不曾孤独过。我所谓孤独,只是求脱出世尘的熏染而已。
评论
隐藏之处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offer:郭律清歌画余生
- 简介:令人心动的offer2郭涛律师和他的小娇妻,内容纯属娱乐想象,不要上升真人
- 0.2万字2年前
- 开局十连抽然后就成世界首富了
- 简介:当分手的林辉碰上系统,会产出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火花呢?敬请期待。
- 10.2万字2年前
- 欲望之罪赎
- 简介:每个人都有梦,梦想总是在指引着我们努力向前。但是,如果当你的梦想中夹杂着罪恶的欲望之后,一切,似乎就变得不再那么美好。
- 12.1万字2年前
- 《青云.傲世》
- 简介:《青云.傲世》讲述的是,草庙村的村民被屠杀,张小凡与好友林惊羽,岚彼岸一起上青云门拜师学艺。张小凡,林惊羽,岚彼岸如青云门刻苦修炼,身世之谜一直困扰着岚彼岸。狠毒阴险的师姐田灵儿处处针对岚...《本文来自****,请多多支持!》
- 1.6万字2年前
- 无限穿越系统之沙雕穿万世
- 简介:陆羽再次穿越,穿越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像是要末日了,有说不清楚哪里奇怪,他也许会一直呆在这个世界,也许会离开(纯属虚构)
- 2.1万字2年前
- 话本仙女大本营
- 简介:话本的小仙女们,欢迎踊跃参与啊,奖励丰厚,参与请加QQ群:725118882【进群请备注:书名+笔名】
- 1.1万字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