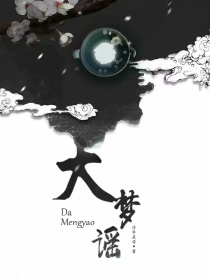第十七章 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
向垣去辞行时,封越正和封乐翎说话。
“拜见陛下,向垣特来辞行。”
封越道:“雨天路滑,向公子何不多待上一时半日,雨停了再走?”
“多谢陛下好意。然向垣不喜拘束,于四方宫墙之内,不过贪一时荣华。待久了,倒有负陛下好意。”
封乐翎笑道:“多少人贪恋荣华都藏在心里,本宫头一回见如你这般宣之于口的。”
鸿雁传书数月的向垣却一副初识的讶然:“这位是……”
“小女宜衡,胡闹惯了,公子见谅。”
向垣当即正色,规规矩矩行礼问安,当作没看见封乐翎不悦的神色,与封越寒暄几句退出殿去。
“朕的小公主怎么还不高兴了?”
封乐翎自然不会说实话,遮掩道:“儿臣可是父皇的掌上明珠,他竟这般没有见识。”
若说没有丁点儿心动,封乐翎自己都不信。
余跃从常来献殷勤,她只觉吵闹。向垣的信一封封送进来,随性的字迹偏能看出字字小心珍重,用素日洒脱掩饰内心不安。向垣很会揣摩人心,知她久居深宫,便将外面的世界写给她看,有时末尾还要叹上一句,被困辰山,极思念外界的景致。
虽是叹息抱怨,却让封乐翎觉得同病相怜,同等心境很是明白,便将书信从头再看一回,想象他眼中的辰山落霞是何模样。
她只在最初回过两封信。
她是公主,向垣最多不过是亲贵,自不愿为一个亲贵的讨好屈尊降贵。向垣的亲近里,未必有半分真心。
可她到底涉世未深,向垣的信里没有一句逾越之语,只是单纯把自己的生活,点点滴滴的欣喜分享给她。不知不觉中,她已然沉浸在向垣描绘给她的世界里。嘴上不说,心里也盼着他的信。
时隔一年,再次见到向垣,她着实欢喜。
然欢喜不过片刻,就被他一盆冷水浇到底,简直自取其辱。
封乐翎心事重重,没注意走到了倚绿轩,抬头怔了片刻,失落气恼更加明显。
玉珠知她心事,屏退其他人,忍不住道:“公主何苦想着他?明明是他先招惹公主,如今却装作初识,还一副……”
“你很希望别人知道你家公主与人暗中来往,私相授受吗?”
原本该离去的人从假山后面绕出来,眼神受伤:“玉珠姐姐当真是错怪我了。”
玉珠上前要同他理论,封乐翎挥手示意她退下,冷淡道:“那你便说说,她何处错怪了你?”
向垣退后拱手道:“向垣是外臣,又是羲国人,不该与公主相识。若非顾着公主名声,来旸国之初便赶来拜见,何苦忍得心焦,一时半刻都坐不住呢?”
一顿,抬眸,深拜:“向垣想见公主,唯这一点,不容诋毁。”
原来这才是原因么……
封乐翎微怔,瞧着他出神,好一会儿才找回声音,轻声道:“若为本宫,你又回来做什么?”
“原因有三,向垣不得不回来。”
“一则,我要与公主说明白,并非存心装作不识,不愿公主误会于我。二则我想将信亲手交与公主,不再假他人之手。”
封乐翎道:“你亲手送,本宫就一定要看么?”
“向垣被困,诸多心事无人诉,我相信公主不是无情之人。”
封乐领不置可否,示意玉珠收下信函,问道:“三呢?”
“三则……向垣在宫里丢了一样东西,回来找找。”
终于松了口气,封乐翎垂眸整理层层叠叠的袖口,眼神一瞬闪躲,随口吩咐道:“玉珠,替向公子找找。”
向垣拦道:“不劳烦玉珠姐姐,这东西,只有公主能找到。”
“哦?是什么?”
勾起她的好奇,向垣得意地笑了,颇有些忘形地上前一步,神秘道:“向垣斗胆,请公主猜上一猜。”
“……要我,猜?”
她在宫里长大,是封越的掌上明珠,当朝太子的亲妹妹,旸国最尊贵的公主,她想知道的事还没人敢瞒她的。如今她好心一问,向垣竟让她自己猜?
见她怔住,向垣笑得更开心了。
他本就生得俊朗,笑起来时,眸若星子,耀眼夺目,如沐春风,教人移不开眼。
“向垣告退。”
“诶!”玉珠急道,“你怎敢让公主猜你的心思?简直放肆!”
向垣眨眨眼睛:“玉珠姐姐又错怪我。向垣今日便走了,不留个悬念,怎能让公主一直想着我呢?”
他退后几步,一个旋身隐于假山之后,不见踪影。
“公主若要找,奴婢派人搜查倚绿轩?”
“你觉得本宫找不到?”她反问,回头又见她手上信笺,“收好,别让人瞧见了。本宫与他,只在父皇的书房有过一面之缘,记着了么?”
“是,奴婢明白。”
质馆书房,段回峰无奈地看着向垣。
“表哥,我这就走了,你陪我出去玩嘛。”
向垣坐没坐相,双手一摊占去大半张桌子,闹得段回峰连喝两盏茶都压不下心头烦躁。然一对上他期待的眼神,身后那条无形的蓬松尾巴摇来晃去,扫走了想骂他的心情和未来得及说出口的狠话。
“你都要回平城了,还怕没人陪你玩?孤对这里不熟,你找沈轩泽,封翼,哪个不行?”
向垣哼一声,扭过脸去不看他。
“他们算什么?啊,我明白了,表哥是嫌我吵闹,撵我走呢。”
确实。
然而这话他只敢在心里说说,让他知道还不定怎么闹呢。段回峰只庆幸向垣不是女子,不然依着两家情谊,早早许了太子妃之位,将来天天在一起,不知会是怎样的头疼。
虽然……
他看看向垣,连掩饰都不想掩饰了,重重一声叹息,体会到了向城的难处。
虽然现在就已经很头疼了。
昨日宴上,初次现身的二公子与传闻揣测一般无二,尤其是权倾朝野的傲气和对向垣的宠爱,除了最初分给封越两个眼神,注意力全在向垣身上,直到散席。期间有人敬他,也全作不见,目空无人,经向垣提醒,才敷衍地抿一口茶,矜傲与偏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封越不说,众人也心知肚明,一年前的将军府灭门案与他脱不了干系。经由昨晚,不知多少人要来巴结向垣,他怎么会没的玩?
谁料他拿这话去堵他时,向坦义正词严,讲起了道理。
“他们各怀鬼胎,必定有所求。我若应邀去了,不是给二哥添乱么?”
说这话时,段回峰正饮茶,一口气没上来,咳了半天,震惊道:“不给他添乱,就能给孤添乱了?他是太子孤是太子?”
向垣讨好卖乖道:“自然是表哥啦。表哥是太子,这点麻烦算什么?是不是?”
缠了半晌,这会儿向垣已经开始耍赖,趴在他书桌上寸步不让。
然他到底不想再耗下去,局势日渐紧张,他自然没有闲情去玩,更没有向垣那么好的兴致。
鸣蝉吵闹,他可以让向境把蝉粘去,难道还能让他把向垣粘走?
对了,还有向境。
段回峰长舒一口气:“向境。”
“属下在。”
“你,陪他去。”
“啊?”向垣站起来,连连摆手,“不要不要,我还是等闻生回来再……”
“一刻也不准耽搁。你在这里,只会扰人清静。”
眼见段回峰失了耐心,下达最后通牒,向垣也不敢造次了,悻悻出门,坐上马车,到了来雁楼专门留给他的雅间。
“跟着表哥就是比在向府好,你与从前可大不一样了。”
向境似是很不习惯和向垣单独相处。尽管向垣摁着他坐在对面,他也只低头不语,盯一会儿衣摆上的暗纹,盯一会儿茶桌边沿的雕花,袅袅热气挡在他们两人之间,像一堵隔在心间的墙。向垣端走吹散,向境还是不自在。
听见向垣闲话,他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
正巧沈轩泽听说他来,念着几日前请他听戏的意外,赶来问安,倒解了他一时之困。
沈轩泽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跟着一位姑娘,水绿罗裙,外罩素白纱衣,衣襟袖口盛着杏花烟雨,婷婷袅袅迈着碎步,清丽面容略施薄黛,抱着一把琵琶走进来。
“前两日的戏不合公子心意,小民特来请罪,还望公子赏脸。”
向垣放了茶,一手摸到腰间折扇,轻扇两下,细细嗅过,玩味道:“姑娘身上好香,沈家哥哥有心了。”
二人对视,皆有些慌张。
沈轩泽拱手强笑道:“公子说笑,小民怎担得起?”
向垣不理会,垂眸饮茶,递给向境一个眼神。
向境轻声道:“沈合欢。平昌侯沈允幼子之女。当初封越称帝,沈文潜见罪于他,被处以死刑,尚有身孕的沈夫人逃往农庄,生下一女,难产而死,被当作畏罪自尽,故无人知晓沈姑娘的身份。她是沈侯流落在外的嫡亲孙女。”
“公子院中无人,是我家将军该思虑的事,不劳沈公子费心。”
他的声音极轻极细,徐徐道来像在讲故事,说的话却不如故事般美好,令人生寒。
沈轩泽没想到连这种事都被查清了,手心冒汗,语无伦次,颤着声音:“不,我,不是……”
“我倒无妨,沈家哥哥既送沈姑娘来,便不怕本公子临时起意将她带走。可出来时,表哥让他作陪。若回去时沾上什么香,染上什么料,亦或者这曲子听进心里,魂牵梦绕了……沈公子说,如何是好?还是你留下陪我,遣他回去?”
雅间内,向垣悠闲自在,丝毫没有因为沈轩泽自作聪明的做法不悦,向境低头不语,二人大气不敢出,一时只有杯盖划过杯身的声音。
向垣抚着茶盏,语气恍然,面上却是一副看戏的模样:“啊,许是我忘了说,他不只是表哥的侍从,还是我的庶弟,沈公子怕是使唤不起。”
太子近侍,向家公子,无论哪一重身份他都使唤不起。
一滴冷汗划过,沈轩泽的手微微发抖。
“三公子……三公子实在多虑了,小民怕公子无趣,才特让小妹弹曲作陪,万不敢有别的想法。”
向垣恍然大悟,一拊大腿:“原来如此,竟是我误会了。向境,代我去沈府赔罪,本公子要留在这好好欣赏沈姑娘的琵琶技艺。”
随风入境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宫廷逆袭传
- 简介:本文禁止转载,一经发现追究法律责任!傻白甜慎入!玛丽苏慎入!这里没有山盟海誓。没有三千佳丽只爱一人的痴心帝王,只有诡计、阴谋、心机和杀人不见血。女主穿越回古代宫廷废后之身,面临着杀机,阴谋,真假闺蜜,看女主逆袭,在冷血的后宫反败为胜!而她又能否再赢回她的爱情?本文故事背景为架空朝代,文中朝代,妃嫔位分,地名,药方等皆为虚构。架空背景即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接轨的平行宇宙,本故事纯属虚构,所有情节只为推动剧情发展,请勿与历史相提并论。讨论剧情欢迎联系493153175@qq.com
- 46.2万字2年前
- 穿到古代扶贫种田
- 简介: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订婚宴当夜,许萱芷被炸死,意外穿越到古代。谁知古代的日子也不好过,榜眼爹惹圣怒被贬了,一家人由繁华京都被谪贬到贫苦边远小山县。许萱芷:就当我跑古代来扶贫种田搞基建吧。至于,书呆子爹不通俗事?许萱芷:娘,外祖父,爹就交给你们调教了。一家子不会种田?许萱芷:祖父祖母,高产粮就交给你们了。……(第三个坑开张,欢迎各位同时入坑,小有存稿,入股不亏。)
- 8.1万字2年前
- 大梦谣
- 简介:“拜见上神”初见流光仙君的时候,挽笙九万岁。看着眼前的男子,她只觉眼熟,却又不知在何处见过,于是淡淡点头,擦肩而过。然而便是这样一眼,牵引出多少后事,几经世人流传,最后只得这样一句:回首空忆前世梦,骤然断肠大梦谣。
- 1.1万字2年前
-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之冤案迷途
- 简介:喵星上的一个小队,这个小队专门为冤案鸣声。他们无法阻止冤案的诞生和受害者的死亡,但他们可以及时找到证据,还冤者一个清白,也让那些冤案沉冤得雪。
- 0.4万字2年前
- 宸痕天下
- 简介:来自六十九世纪的冷艳杀神女皇墨宸去盗取有着惊天灭地力量的未来之心,结果却因吸取未来之心而穿越到圣光大陆的凤羽国,成了无痕公主,这就算了,居然穿到三岁多的小屁孩身上,好在,有父皇母后的宠爱,哥哥百般的疼爱,满足了她对这副身躯的不满,但是总有一些不知好歹的家伙来挑衅,好,本公主就陪你玩玩,看看最后谁才是胜利者。狂妄霸气的祁玄国太子,温柔体贴的莲昕族世子,妩媚腹黑的天阶灵力男子,善良纯真的医学天才,谁更能立她心动呢?看杀神女皇如何斗渣女,收美男,练得绝世武功,成就女皇之路
- 0.0万字2年前
- 伍六七——沙雕校园
- 简介:这是柒梅校园文,柒梅恋,柒白党可进可不进,自己看着办
- 0.5万字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