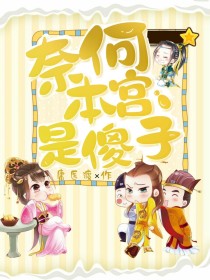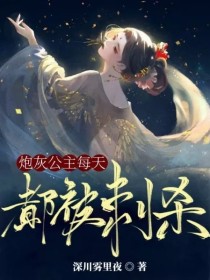昆仑
猗嗟娈兮,清扬婉兮,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
景清王赵璿亦是那名动天下的“四璧之一”,称之昆仑。
谢珩看着眼前,这稍显落魄,却又不失风采的俊美公子,有些恍惚。
一身沾满风尘的青衫,八尺的身量,背挺得笔直,发鬓微乱,几缕青丝垂在额前。
他眸中带着笑意,略微上挑的眉眼是属于逍遥的风流。
谢珩跟着他进了里屋。时隔两年,年少旧友也不知该如何开口。
年久失修的茅草房,曹副只来得及把蛛网陈灰拾掇拾掇,桌子蒲团也没有置上。
赵璿围着谢珩转了几个来回,见他一身行头比自己还要狼狈,一双眼睛跟着自己的身影转。
眼角带着戏谑的笑意:“珩弟倒是变了许多,愚兄都快认不出了。”
跟前的人,肤色苍白,面颊上还有未揩去的沙粒。
谢珩无奈:“不比原来。”
两人东拉西扯聊了两句,最终绕回了重心。
赵璿道:“匈奴最近有动作了?。”气氛瞬间凝重起来。
“嗯”谢珩如实说道:“我上月递呈了一份奏折,将匈奴动向与阿朗道明,却迟迟不见答复。”
赵璿蹙眉,沉思片刻,复而看向谢珩:“不必再递呈折,开战之时,我寻个法子让你脱身,带着谢家一齐,退去江南。”
谢珩一惊,微垂的眼眸瞪大,似乎在头脑中,不断地确认方才赵璿说的话。
江南一带,楚氏的势力盘根错节,虽多为商贾之行,却不可小觑。
“江南有楚家在,杨诏的手还伸不到这么远。”谢珩听着,心下也盘算着其中。
匈奴两年前会休战,是因喀什单于暴毙,王帐内乱,不得已才喊的停。那时,匈奴的大军已兵至暄夕城,谢桢留守。
三十五万兵马,对上三万谢家军。守城、监军携着贵族子弟兵,落荒而逃。若不是还算有些良心,留了三日粮草,恐怕谢家军还撑不到匈奴退兵那日。
两年的时间,喀什的胞弟达格摩上位。据掌握的情报来看,达格摩的野心并不亚于他的哥哥,更有胜于其。
“我委托罕罗沙漠那头的乌邦朋友打听过,达格摩已经筹备好了兵马粮草,恐来势汹汹。若我退去江南,那旻朝必定不保!”谢珩沉声道,面色稍霁。他缓了过来,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岂不是自掘坟墓?
赵璿叹了口气,晃了两下头:“珩弟还不明白吗?”
谢珩默声,依旧沉着脸。
“支离破碎后,百面各异,却终究是为一体。”
一面镜子跌落,摔得粉身碎骨,但是大大小小的碎片,映着的,拼接在一块,是永恒不变的江山。
“残破的宫阙需要的不是修补,是倾覆。而倾覆,不过是为了重筑罢。”
……
先出来的是谢珩,他皱着眉,神情复杂。曹副不知他们聊了什么,见后出来的赵璿,脸上依然挂着笑,朝他颔首。
一路无言。赵璿不着痕迹瞟了眼谢珩,与自己来时,所想象的模样不同。谢府二郎应当是霁月光风,一颦一笑间温和得体。
赵璿欲言又止,最后道:“惜辞,一切以大局为重。”
回想着茅屋里,谢珩说的话,赵璿也不知到底该如何答复,只能模糊说个顾全大局。
谢珩轻声应了句,朝赵璿略微颔首,全做礼数。
“王爷,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同意,兄长更加不会同意。江山社稷之事,并非只是朝堂之上的争权夺利,马虎不得,胆大不得。”
他懂得了赵璿的意思。
可他不愿这般做,这样无非是将百姓黎民至于水深火热中,只为全了那点权势。
赵璿:“确实是愚兄鲁莽,但依如今形势来看,我们似乎也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又一声绵长的叹息,像是穿过山林,遥迢千里赶来的春风,春未生,已陈秋。
他何尝不希望只做个逍遥的闲散王爷,不过问政事,结交几个狐朋狗友,附庸风雅,在王府中混吃等死。
生不逢时乃不幸,心有所系为万幸。
要不是他有个做皇帝的弟弟,心上人是个将军,他才不会把自己扔进权力的染缸之中。
“王爷知道谢家军,建军至今已多少个春秋?”
“两百三十一年,戍守西部两百一十九年,八代谢家人,五十万谢家军。大大小小数百次战役,四十万将士魂客异乡。”
“王爷,你说谢珩能退到何处去。”
谢珩是这般回答他的。
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西有匈奴野心之大,西南有突厥之患,东方远洋之外还有尤斯虎视眈眈,何况朝野霍乱,谢家军难免陷入两难的局面。国人杀国人,外贼杀国人。”
“惜辞,我们没有余力了。”
“谢家军声望再高,再是赤诚,可终究是暮年残辉,大势已去。”
“惜辞,朗逸还在等你归家。”
归家……
归家。
若是前路坦荡,日正烈阳,他又何必在这茫茫塞外,与他相隔万里。
灵均阿兄,珩,回不去了。
谢珩心中如是想着,不肯出声。
大漠的天越来越沉,风沙挡住了华光异彩的晚霞。
听谢桢提到过,那晚霞似乎是古幽关塞最美丽的景色。
火烧般的滚云从更远的西边涌来,赭红色的霞光自滚云后蔓延过半边天。似是千军万马来,马踏如雷,卷起万丈风尘。
可惜今日不能得见。
赵璿负手而立,站在都护府内院之中。
天色渐灰,从夜幕中走来一道身影。灰扑扑的长衫,白边衣襟处绣了几簇,色彩浅淡些的朱槿花,领口轻微磨毛,想必是洗过多次导致。
许是暮晚的原因,那人的身影淡得像是经年的墨画。
赵璿看过赵玗为谢珩描的像。没有点色,只是用了石安坊的墨,草凝堂的纸,数笔描摹。
来前,他又看见了这画像,就摊在赵玗的书案上。左边是一沓未曾著名的书,右边就放着这画。
两年去矣,石安坊的墨褪了色,草凝堂的纸磨损了页脚……
谢珩缓步而来,对赵璿躬身一礼,手中奉上一卷册子:“这是谢家一百士兵的名册,何时入军籍,故乡何处,杀敌几何,皆在此中。”
赵璿接过,也没有着急翻看,而是问道:“你可想好了?只一百谢家军与我退去江南。”
谢珩垂眸,微颔首。
与赵璿一同回都护府后,与他对坐许久,最终还是退了一步了。
赵璿说得没错,江山欲颓,大势已去,谢家军是最后的支撑。
可他自己也没错,山河飘摇,外患四伏,谢家军是边关的第一层铁墙。
“嗯,一百人。他们善战,严守军纪,知晓什么是国,什么是家。若他们打理军营,操练士兵,不会比我差。”
“时至此今,边关不可无谢家。”
他姓谢,他名珩,他字惜辞,他号南红公子,他是旻朝的将军。
太平令(原:南红公子)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重生:疯批暴君他宠妻如命
- 简介:【重生+双洁+甜宠+虐渣+打脸】【温软明艳娇气包✘偏执暴虐疯批暴君】前世,她为盛京皇城内名门世家,宁远侯府嫡女,善良一生,见不得困苦与不平,却被世人誉为灾星,而后又因为她的一再忍让,使家中奴仆欺至她头上,她的一再忍让,终是得不到好的结果,国公孙墨殇辞与她自幼青梅,墨殇辞登基为帝,誓要娶她为后,可这段感情不被世人所认可,在成亲那日,被暗杀与轿撵内重来一世,她撕下伪善的面具,这善人,谁爱当谁当,她本以为善事做尽,便是为自己积德,可转念一想,她自始至终,并无得到半点好处,她自幼体弱,横竖都是一死,她为何不为自己活着,她誓要铲除异己,找出仇敌以绝后患,如若她死了,她的阿辞,便没有人在疼了...…………————后来的后来,满皇城的人都知道,新帝有一位放在心尖尖儿上的人,恨不得把整个天下都捧到她面前去
- 8.8万字2年前
- 奈何本宫是傻子
- 简介:苏大白赶了一回快穿热潮,穿越还白捡了一个儿子,本来指望儿子飞黄腾达自己好做米虫,没想儿子竟开局就拿她升级刷皇帝好感度?这儿子不能要了,狗皇帝想谈个恋爱?“陛下,你和傻子说这个不合适。”
- 18.0万字2年前
- 粘人徒弟爱作妖
- 简介:前世萧子夜爱白景宸爱得十分卑微,陪他威震四海,助他叱咤朝堂,却得到他的无情以对,害的他国破家亡,甚至连在死时都想着替他铺平未来的路。重活一世,他决心不再与白景宸有任何瓜葛,却不想曾经那个高冷的徒弟不知从何时开始已经换了一副模样,变得十分爱笑粘人,还总爱撒娇卖萌,撩人不自知,而他却总是对他无可奈何。
- 6.6万字2年前
- 炮灰公主每天都被刺杀
- 简介:「已签约」独家报道:炮灰公主的亡命生涯今天是她诈尸后的第一天,一醒来就被糊了满嘴泥好,她忍。今天是她诈尸后的第二天,差点被熏香熏死,好,她忍。今天是她诈尸后的第三天,遇到“老熟人”,差点被乱刀砍死……哦,苍天啊!再忍下去的话我早晚会死翘翘的!没关系!我们有:精于算计,手持大权的皇兄化作妹控为我们的小公主筹谋划策;掌握未来,致力于改变既定命运的异国皇太子为我们的小公主保驾护航;腹黑毒辣,不要脸皮的死对头,总是莫名其妙的放小公主一马。我还不信我活不下去了——某公主愤怒的一边叫嚷着,一边逃命。
- 5.9万字2年前
- 洛林:皇后娘娘驾到(现代穿越文)
- 简介:那天,本以为无望,竟阴差阳错来到了21世纪……女主和男主回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敬请期待---洛林:皇后娘娘驾到(现代文)
- 0.2万字2年前
- 神尊不好了,夫人又跑了
- 简介:她,是花神;他,是双神(一个龙娇神,一个水神);他爱着她而她却浑然不知在她无助时,是他帮助了他却因为另一个人比他更早遇见她就爱上那个人为了让她多看一眼自己他花了多少精神啊而她却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九世却因为这世那个人比他早遇见她多年后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救了她在他大婚之日她才发现她是多么深爱这个人历经了九世她终于吐露了她的心声“我爱你,佐宇”他为了这句话等了多少年啊终于这一句话
- 1.1万字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