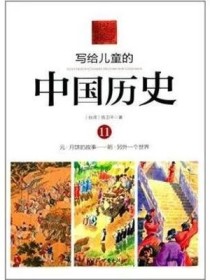坂口安吾《论FARCE》节选四
闹剧是要全面肯定人的本来面目,如此一来势必不会关注人的个体性格层面,而是要从本质上来把握人,结果很多时候就会变得极为概念化、一般化。由此,人物大多是类型化的,情节也很单一,大致都相差无几,甚至连对话的方式、其中的包袱、文章的写作方法等方面都看不出各国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闹剧多对人物做类型化处理,这类人物的典型特征可略举一二,比如他们大多会认为「鄙人真是伟大」「那个年轻人暗恋着我呢」,大都非常自恋。但其实他们并不伟大,也非智者,更非别人暗恋的对象。闹剧的作者非常喜欢用严苛的目光审视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例外。不管人物自恋与否,都不会只赋予人物一种性格,伟大者不会总是伟大,睿智者也不会一直睿智。哪怕是「这个家伙比那个家伙更机灵呢」这种程度的评价标准,闹剧都绝对不会提示给读者,类似于「那个家伙蠢透了」这类的词句,闹剧是绝不会说的。再有,举例来看,闹剧的人物很多时候都会大放悲声说「鄙人真是悲惨,我的命运实在太残酷了……」之类。但是,闹剧的作者们往往对这类悲叹毫不在意,对这些悲伤的皮埃洛或是斯嘎那勒尔之流不加干预,仅以严苛的目光审视之。闹剧的作者绝不会去同情任何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他们顽固得就像木头人,像木桩、电线杆一般,完全拒绝敞开心扉。因而通过对一切事物所持的这种冷酷和冷漠,达成了对一切事物的肯定。这一悲情手段是闹剧作家必须领悟、坚持的金科玉律。
从根本而言,闹剧向来都是最爱卖弄、浮夸的(属于不伦不类没做好的)文类,不分国别。但是在西方,到了近代,闹剧逐渐变得具有科学性起来———这样说也有些夸大其词,换言之,闹剧的整体结构变得甚是合乎逻辑起来。于是,在措辞方面反复雕琢以求合乎逻辑,此举使得闹剧的文章做法似乎也在努力排除掉那些不知所云的混沌。
但是日本的情况却和西方正好相反,历史最为悠久的狂言的结构最具逻辑性,在人物处理上也和西方近代的情况最为相似。
西方近代逻辑性的闹剧写作方法本质上其实极为单纯,就是在「A 是 A」「A 并非不是 A」这类最为单纯的法则之上,以此为基调结构而写成。修辞且不必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整体来看也都运用了这一法则,非常明显。以马塞尔·阿沙尔的《请和我一起玩吧》为例,稍稍翻阅任何一页都能清晰地读出这一点。但是,这种逻辑性处理非常容易陷入僵局。阿沙尔也是这样,他很早就遭遇到了瓶颈,最近正试图转向更为个性化、更为现实的喜剧创作上去。但是他尚未充分把握好闹剧和喜剧各自在文章处理上的特征,所以好像既非喜剧又非闹剧,和两者都若即若离、游移不定,最近的作品大都没什么价值。
散装书摘与文摘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银函的一些破烂文章
- 简介:就是一些破烂文,杂七杂八,啥都有。[图片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立即删除]
- 0.0万字2年前
- 文司:彼岸
- 0.7万字2年前
- 当青葱已成过往
- 简介:曾经岁月青葱,奇思妙想,天马行空,快乐无忧却强赋愁。而今不再年少,辗转奔忙,柴米油盐,千头万绪却道好凉的秋……
- 6.3万字2年前
- 青烟茶馆
- 简介:第一部:0107号实验体的惊险打工人生活第二部:0107号实验体的忙碌师门生活第三部:0107号实验体的悠闲养老生活
- 0.3万字2年前
- 今夜不再(君故同人文)
- 简介:(首先感谢清粥沫笙太太给我了这个允许写《君故》同人文的权利!你要问《君故》是哪个作品就是《太阳赋予我们的光辉历史)(另外清粥太太的扑克牌设定真的是巨好看!)主要以布尔拉提的视角展开,因为埃里克瑞克魔法的失误而进入扑克牌的世界观念并且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和众人的另一面不为人知的秘密
- 0.0万字2年前
- 世界的故事?
- 简介:从上古神话到如今世界,到底历经多少沧桑?嘘....马上开讲
- 0.4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