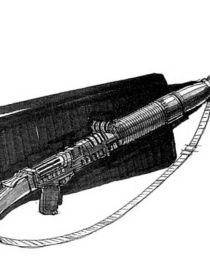第六章
我发觉自己叫战友叫早了。
火车每停一站,就有干部来车厢点名,被点到的人要拎背包列队下车。窗外景色越来越荒芜,火车到站有时在凌晨,我睡梦中醒来,和剩下的人一起挤在窗边,荒野中没有灯火,方圆十里已看不到人烟。
“战友、同志,小兄弟……我可以坐过去吗?”
六个人的位置现在只剩两个人了,我们隔着桌子对望。一路上我都一张冷脸,其实心里也落魄得不行。我刚一点头,他就自来熟地搂着自己的背包颠颠凑过来,唯恐我反悔似的。
“战友,我叫江涛。”
江涛是最早分牛肉干给我吃的那个人,我虽然不和他们说话,但这些都记得。我俩这面的窗户碎了个角,平原上月色如镜,我夜里睡得牙关打颤,江涛就靠过来和我一起哆嗦。
这列绿皮火车最终停在了铁轨尽头,我诧异地看着这座漫天黄沙里的老式车站,心想它快和老陆一般大了吧?我瞥见连一路爱说爱笑的江涛都在偷偷皱眉,但他转向我时又带了个灿烂的笑脸。
“怕什么?百坡,我们是老乡,哥哥我要罩着你。”
混着猎猎风声,说要罩着我的江涛,那时还没过十八岁生日。江涛有一双亮亮的眼睛和一对浅酒窝,嘴角随时都噙着笑意。风沙里,一个黑脸士官吼叫着让我们上一排军用卡车,荒地上敞篷车开得如脱缰野马,我被颠得脸色发青,江涛一手攥拉环一手抱我,居然还笑得出来。
“乖乖、百坡,你要是吐我身上,可得给我洗啊。”
我冲他翻白眼,最终忍住了没吐。
“那群傻-x来了吗?他.妈-的,给老子敲!!这回是真来了!”
这是卡车颠簸着嘶鸣着叫嚣着驶入野战军三五三团大门时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接着耳边炸起震天的锣鼓声,我茫然地看了同样茫然的江涛一眼。
我是被一个急刹车抛出车外的——挡板太矮,江涛没能抱住我,于是我俩滚成一团,齐齐在水泥路上摔了个狗-啃.屎。
从篷车中摔出来,我和江涛头晕目眩中看到路边站了两排老兵,有敲鼓有敲锣,没锣没鼓的一律拿着铁脸盆,看见我们俩的狼狈样子他们连鼓槌都拿不稳了,一个个肆无忌惮地指着我们狂放地跳着笑着。
后来我才知道,这条水泥路是三五三团的英雄道。
一百多个人,站成松散的方队,这一百多个人里我居然个子最矮,被挤在距高台最远的角落。我们的身旁是七八辆轰鸣着的步战车,示威似的围着我们绕着圈转,于是根本没人看高台上的人,一个个全盯着步战车眼睛发直。
高台上有一个戴眼镜的文工干部,和一个铁塔似的军工干部,他们身后是一溜士官。我努力伸长脖子,隔着层层叠叠的人头但再也看不清别的。步战车飞扬的尘土中,高台上的声音传到我这里已经很模糊了,只能默默跟着别人一起鼓掌。高台上文工干部热情地称呼我们“西北白杨树”“献身国防的小老虎”,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多赞美,但无一丝波澜——我脑海里还回荡着进门时听到的那句“那群傻-x来了吗”。
我埋没在人群里,眼睛不住地往身边轰隆移动着的步战车上瞟。步战车的膛管从我头顶扫过,趁炮台上的老兵在睥睨别处,我突然伸手摸向那辆96式的铁壳。
我认得它,陆百年和我提过的、但陆百年没和我提过它有这么烫。
我险些疼出眼泪花,捧着左手在角落里无声地兜着圈跳着脚,没意识到这一刻全场鸦雀无声。高台上,文工和军工干部两名校官身后站出了一名黑瘦的士官,他未经请示,自两米的台上跃下,朝我径直走来。
士官的目光越过人群直视着我,无人敢挡他的路,而从猝然分开的人墙中,我刚茫茫然看到他,士官右手握着份档案袋,嵌钢板的军靴轧得碎石扎扎直响。
他阔步走向我,边走边解武装带。
我那时从头到尾冒着傻气,还在眨眼看着他走近,心里想的是什么时候我才能长得和他一样高呢。
“陆百坡。”
一条阴影划破晴空,武装带兜着风抽在我的脸上。
“陆百坡,要答到。”
另一侧脸上猝然又挨了一记,把站立不稳的我又活活抽得站直。我的帽子被抽飞出三米开外,耳边一阵嗡鸣。
“陆百坡,我是你的新兵连班长严良。”
百坡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大唐开局富可敌国
- 简介:齐明宇:“系统,救命啊!”系统:“要不宿主来个抽奖,怎么样?”齐明宇:“系统,我要买炼钢技术”系统:“去找李世民还钱,要不就来个抵押?”
- 38.2万字2年前
- 李建成x李元吉
- 简介:(究极兄控和弟控的故事)他生于治世,长于乱世,年少英侠,遍交豪杰,世称其为“李天王”,后逢隋末大乱,与父推翻暴政,辅立新朝,名曰“唐”,无数日夜孜孜求索,所忧为社稷,所虑为天下,一朝遇害身后凄凉,武德年间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只为后人留下一桩玄案和几桩笑料,可谓“英雄折戟,宝剑沉渊”,孤坟不见雪,无处话悲凉。(多平台发布)
- 9.4万字2年前
- 土客
- 简介:“慨夫生民多艰,徒增琐尾之忧;聚族頻迁,仅获鹪鹩之寄。万千人而穷居异域,千余载而终为战场。"谨以此书唤醒人们心中早已被尘封的记忆,同时哀悼因那场尸横遍野,流血漂橹的战争而逝去的人们。“低头读历史,仰首望天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4.8万字2年前
- 和尚传奇
- 简介:谢谢观看
- 0.4万字2年前
- 魏国风云
- 简介:本书讲述在战国大争之世,魏国百年霸业,兴衰荣辱。
- 1.2万字2年前
- 中央星系:机动特遣队
- 简介:这不是地球,却有与之相似的文明;这里的科技高度发达,却与魔法并存;所有在地球上的"科幻"在这里似乎都能变为现实。在这里,有一支小队,正借着夜色的掩护,奔赴下一个目标……(本人高中牲一枚,毫无写作经验,还请诸位轻点骂~)
- 1.2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