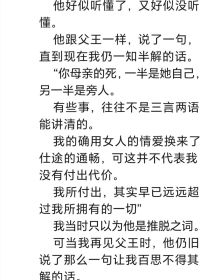番外篇 焚琴煮鹤百年身
咸宁五年,这一年,宋衎守孝期满,除丧服,入朝为官。
临去之前,他最后一次整理了父亲的遗物,三年里,他遵循宋蕴之的遗愿,该烧的烧了,该捎的也捎了,留下的,“行之,往事不念。”宋蕴之只余下这一句话,宋衎揣测,最后留下的恐是些父亲在前朝当职时的故友互赠的物什。
古往今来,物是人非,天地间,唯有江山不老。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了。
一只缺了一角的明制象牙笏板,几卷书,一把画扇,一身明制绯袍,一只金镯子。
镯子是天聪年间宋蕴之命人从象牙笏板上扣下来的一块镶金,熔成一只金镯子,形制只有纤细的女子才能戴下,他交予宋衎,说:“你若将来有心仪的女子,便拿此物赠予她罢。”
其实这枚镯子一直由宋蕴之收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宋衎以为父亲是这个意思。
直到宋蕴之临近去世那几年,宋衎才对这枚镯子的来历起了疑心。宋蕴之从前身子就不好,经年风沙颠簸,已是一身病骨,那些个深夜里风湿侵梦的时日,宋衎半夜起来倒茶喝,听见父亲房中衣物摩擦的声响,宋蕴之是打碎了牙往肚里咽的性子,平日里便少言少语,即便痛得不能自已,也只是辗转于床侧,不溢出半点呻吟。
宋衎放心不下,悄悄捅穿了窗纸,窥探父亲的情况,那个角度,他只能看见宋蕴之一只瘦如枯枝的手搁在床外,他的小臂青筋盘虬,指关节因用力而苍白,掌心紧紧攥着那枚金镯子。
那只金镯子,在寒冬腊月冷冷的月光下,闪着比往日都要明亮的光泽,在父亲手中,如同溺水之人攥住岸边的水草,此时的金镯子被赋予一种信仰得救般的神性。
他想,莫非这件,也是前朝故人的遗物?一位女子的遗物?可宋衎分明是亲眼看见这枚镯子,是宋蕴之命人从笏板上扣下来的,本就是父亲自己的东西。
宋衎不愿再揣测,他不忍心捅破娘亲和父亲之间相敬如宾的感情,宋蕴之此生只娶了邵家嫡女邵涓,不立侧室,感情深厚,宋衎不愿信,娘亲苦心经营,捂热的石头,曾经主动捂暖过旁的女子。
他从此看那金镯子,倏地就不顺眼了。
岁月是留不住人的。
天聪十八年,宋蕴之上疏,乞骸骨,告老还乡。
天聪十九年,陛下驾崩,新帝登基,改元咸宁。
其后二年,宋蕴之卒。
宋蕴之离去时,早已缠绵病榻数月,眼窝深陷,气息腐朽,唯有衣衫雪白——哪怕昏睡,他也能勉强挤出一丝清明,嘱咐邵氏给他更衣。
彼时众人皆知宋蕴之气数已尽,宋衎守在蕴之床前,陪着他艰难地喘息。回光返照的那一刻,宋蕴之黯淡的眼中辗转出宋衎从未见过的光华,透过自己,透过屋室,目光落在虚无的某处。他从未见过父亲有过这样的侧面,仿佛时间倒流了几十个春秋,在万头攒动火树银花的长安街头,宋家有子,策我良马,被我轻裘,头戴梁官,朝服似霞,眉如山川,目比剑光,那是徒手遮风雨的光彩啊。
宋衎知道宋蕴之必然有所交代,忙唤邵氏进来。
“怀瑾,怀瑾……”他短促地喘息,面上泛起诡谲的红晕。
怀瑾是谁?
邵氏一愣,顿在门口,双手绞着衣角,不知所措。
他这些年克己复礼,如同经年深井里的凉水,从未有过这样的语调。
“怀瑾,听鹤也是同你一道来的?”宋蕴之扭头,转向宋衎,目光却不触及,他仿佛不是在望着宋衎,而是隔着十几年,几十年的光阴,望向过去。
宋蕴之仿佛听到了回答,嘴唇张张合合,眼神像是要从虚空中攥取某物,确实竹篮打水一场空,声音微若蚊吟:“蕴之,无颜见你们。”他仰头望向头顶,床顶的雕花繁复压抑,一如望向命运。
“但蕴之此生……”他整个人颤抖起来,牙关咬紧,耗尽毕生气力,邵氏忙上前帮宋蕴之拭去汗水。
“此生,不敢忘国。”
落日的余晖收尽苍凉余照,从山顶平静地走下山坡,死亡于他不似终点,而是新的坦途。他这一生,早已走过了太多终点。
宋衎眼睁睁地看着宋蕴之的目光再次颓废下去,如同燃烬的烛芯,一点一点灭掉最后的花火。
“行之,往事不念。”他叹出一口气,也是今生今世最后一口气。
咸宁二年,宋衡不禄,谥号文济。他走的那年,暮春三月,京城开了新制,新帝厉行改革,轻徭减赋,百废俱兴,身前所憾,皆成身后之事,宋衎不知这算不算得上功德。
宋蕴之的生命底色如同江南枝头虚弱的春色,尚未转青,春已迟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衎听闻,父亲从前是前朝一手遮天的不世之才,是三法司里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明律法的化身,是绥祯帝身边百算无遗的谋臣,是天徽年间风光无限的宋家长子状元郎。宋衎寻思着,父亲回光返照时的模样,兴许就是他当年的一二风华。
可自大明亡后,天聪年间,满人轻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宋蕴之一路迁官,他本该留在京城挥斥方遒,可却离京越来越远。
天聪五年,适邵氏摽梅之年,娉娉袅袅,仰慕已是三十而立的宋蕴之,二人结为连理,次年生下一子,起名宋衎,字行之。
邵氏端庄自持,蕙质兰心,说话轻声细语,宋蕴之同她言语时甚至会放低声音,邵氏的面颊便羞得红了。
从宋衎懂事开始,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告诉他,即便家庭美满,父亲的心也是灰的,想也不奇怪,若是天生惊世之才却沦落沧海遗珠,心自然是灰的。
院落中间种了一株红梅,听下人说,是按宋蕴之的吩咐种的,他宝贝得很。
可是宋衎从未见过这株梅树开花,先前父亲找花匠来瞧过,花匠说,这屋子的风水不好,梅是养不活的。
邵氏在一边发了怒气,道,府中旁的花都能活,为何偏偏红梅不能活,你没学好本事,某要空口无凭地咒宋家。
的确,母亲欢喜的红药每到时节,都开得正好,院落中唯一倔强着不肯开花的,只有红梅。
“罢了,不能开花,便不能开罢。”
父亲结了工钱,请走了花匠,他甚至没问有什么法子能让红梅开花,只是宋衎能察觉,父亲的心,又灰了一点。
院中央的红梅,确切地说,若是在府邸中不能开花,它只是一株寻常的杂草杂树,邵氏浇花时都刻意厌弃地略过,只有宋蕴之,好些时候命下人搬来一把摇椅,他坐着读书,对着不开花的红梅。
国子监下学,一日宋衎问宋蕴之:“父亲,你可是在等红梅开花?”
宋蕴之坐在光影里,低垂的夕阳映射得叶影落在他面颊上,眼帘低垂,眉骨钝而突显,他远不如从前意气风发了,甚至称得上落寞,只是矜贵尚在,高傲尚在。
“非也。”宋蕴之道。
“那,父亲为何不将这红梅换处地方,偏要摆在院落中央,若是同母亲一般,在边角种些花草,兴许能开花。”宋衎自诩聪慧。
宋衎咂不出父亲的神色,只觉得哀伤。
“宋衎,花开花落,自有时。 ”
天聪十七年,此时距宋蕴之告老还乡尚余一年,朝中
孤城绝越三春暮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深宫忆往昔
- 简介:宫门深深,我悲我喜,故念卿卿。。。
- 12.9万字1年前
- 芸汐传2(天才小毒妃)
- 简介:芸汐传
- 0.9万字2年前
- 关于反派的千层套路
- 简介:许华叫了自己干弟来宫中混淆视听,而后使了一计金蝉脱壳,放把大火逃之夭夭。他的外籍身份早已被当今大太子请命转为本地。这样一来他回去就能开个府再娶个老实的婆娘安心过日子。但许华偏不,在都城近处某个隐蔽的角落依傍着干弟留下的足量财产开了家当铺。登基之日杜晓毫不意外被推上帝位,这时许华改名换姓地出现了。并义正言辞地冲杜晓大吼:“你傻吗?”
- 0.5万字1年前
- 虐渣皇后
- 简介:一直虐渣,一直爽
- 0.1万字1年前
- 卿卿可谓颜如玉
- 简介:“阿照,若你想做妖王,我便将这王位赠与你。”“若你不愿做这妖王,便做我的王后吧。”
- 0.3万字1年前
- 闻琢献
- 简介:因为轻素,我困惑半生。
- 1.4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