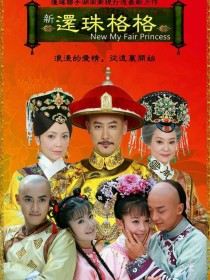(一百七十六)战栗
(天知道我怎么那么热衷于换鬼蛊的封面。)
————
话题转得快了点,他一顿,拿起最后一支烟正要往嘴里塞,手悬在嘴边又放下了,手收回在膝盖上摩挲几下,回忆半晌,回道:“好像还存在殡仪馆。在监控里截出他的照片发了寻人启事,也没人来认领。是一个伙计去办的,这两天我们光围着你转了,也没顾上那边。”
我点点头,不再问,看着病房外。他讲了太久,嘴里没了烟好像突然不习惯在我面前待着了似的,摆什么姿势都看他有些局促,最后干巴巴叮嘱几句让我别抽烟别乱动好好休息,一推凳子快步出病房,急急如逃犯。
是逃我、逃这件关乎背叛的事、还是逃他自己。不知道。
我坐在床上看他合上门,门上明亮的小窗户映出他黑风一样一拂而过的影子,又回归空空如也。暖黄的光线透进来,柔得像阳光揉着月光。
我试图透过窗户寻找那抹来自皮衣的熟悉的黑色,失败了。
又等了一会儿,于是开始轻声地唤“黑爷”,我知道再轻他也听得见。唤到气短,转成轻声咳嗽,因为虚弱,那咳声也轻得像下一口气就再难吸上来。
其实最后两声咳已经是装的了。
我是太骄纵了些,骄纵到跌跌撞撞走了这么些年,早忘了什么是纯粹的信任,可仍笃定他会心疼我,笃定得超过笃定明日会升起朝阳。
门果然被推开了。来者短暂地遮住小窗的光,又肩负着光走进来,墨镜反光,整个人笼着暖色的描边,可惜神情还是冷得像周遭消毒水的味道。
他在床头倒了杯温水递给我,然后转身就又要走,被我扯住衣角。我自以为用了些力了,没想到指尖像不是我的,完全没有力道,他不过往前迈了半步,衣料就从我手中溜出去,游鱼一样。
手拉不住了,我不想他走,就又轻得梦呓一样唤。
“黑爷……”
已经是我求他时才会有的语气。他很多年没听到过了,立时一顿,垂在身侧的手指蜷了蜷,不知想握住什么。
我的虚弱和服软到底牵住了他。我听见他微不可闻的叹气声,然后终于回头,坐在我床脚,还是不说话,缄默得像换了个灵魂。
我吸口气,开口:“我太少见你冷脸了。你生气也会笑。别这样。”
说完又想起现在理亏的是我,于是又轻声加了句,“行么“。
他不回。我便故意做出要起身往床尾挪动的动作,他果然立刻起身按住我,不让我再动。
我得逞,手覆在他按着我肩膀的手上。我的手凉到没有生气,他果然没有躲开,任由他手心的热气传向我。我慢慢牵起他的手,贴在我脸侧,半闭上眼睛。直到我终于被这只熟悉不过的手染上了些温度,我又用我没什么血色的唇在他手心轻轻一吻,轻得瘙痒。
“真的,别这样。原谅我吧。我现在好疼,疼就会多想,多想就会怕。怕你不要我了。”
语气软得像绸缎滑过唇瓣。
我没睁眼,我只是等。
倒也不全真的那么想。和爱人玩弄些无关紧要地心计是所有女人都爱做的么?反正,我现在是如此了。
等到了,而且没有用多久。稀落的光线下,那只带茧的大手开始慢慢抚摸我的脸颊,像此生第一次见我一样仔细。略过脖子的伤口,又移到指甲划痕已快痊愈的后颈,暖意从他触过的地方一路传到脑海深处。
他才是我的药罢。头疼突然就轻了。
我在他的吻落下的一瞬间睁眼。我不信他没看见我眼中露出的一丝得逞后的狡黠,但他只是一点点,雕琢一样,又轻又慢地加重那个吻。
相爱之后,从未吻得那么缠绵过。情浓时我竟又感到他在我的肌肤上的手有非常微弱的抖。也许只是错觉,雨村口树下他的颤抖还没在我心里消解。
就算他真的在颤抖,那想是来自想把我揉碎进怀中又要控制着不能用半分力道,从而无处发泄的爱惜。和种种只有阅尽我们的故事之人才懂的汹涌感情,如钱塘江的大潮。
那或许就不是颤抖了。
是战栗。
盗笔衍生:鬼蛊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综穿之时间旅途者
- 简介:不存在的学生会长裘球*面瘫古板的中万钧(完)人间神明张起灵*狂热粉丝丧丧子(更新中)武魂殿第五供奉光翎*被召唤的少女胡列娜(待更)
- 34.5万字2年前
- 新还珠格格之泰萱恋
- 简介:第一部《新还珠格格之心有所属》重要通知:我在这里和喜欢心有所属作品的读者说一声抱歉,因为和我的这部作品相似所以被强制下架了,我已经尽力去争取恢复了,但是还是不能,很抱歉。如果可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泰萱恋,真的很抱歉
- 19.9万字2年前
- 综影视:乱你心扉
- 简介:长月烬明正在更新中【病娇魔神澹台烬✖️温暖神女蓝星榆】蓝星榆借助过去镜多次穿越,与景国质子澹台烬从相识到相爱。却不曾想这神器使用过度还有副作用,将她困于其中无法逃离,身陨其中。也不曾想她的离去令这位柔弱质子堕落成魔,翻遍三界寻着她的身影。“澹台烬,以后我都不走了,永远待在你身边可好?”“好,自然是好的。”“为什么你要不告而别?”“对不起,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绝对不会如此。”“好,只要你说的,我都信。”
- 45.8万字2年前
- 惊封:我是反派女儿
- 简介:白六在厕所里捡到了一个婴儿,谁知她是个白眼狼?“小桃要救他?当好人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会哦~”“父亲也当好人了,父亲把我带回去养着了”“父亲可是做了件好事所以才金钱流失快,你看父亲这不不好了?”“不止哦,父亲还收获了一个白眼狼”白六笑着摸了摸白桃毛茸茸的头“呵呵,知道就行”
- 6.8万字2年前
- 长月烬明之选择
- 简介:前因后果几世轮回三生三世皆为我选择
- 4.4万字2年前
- 综影视:拯救意难平男二们
- 简介://长月烬明//爱情而已/黑暗荣耀/少年歌行/星落凝成糖/重紫/狂飙/(开后宫ing)1.星汉灿烂已完结(袁慎×程少商)2.说英雄已完结(少将军×大小姐)cp白愁飞3.苍兰诀已完结(仙君×神女)cp长珩4.星汉灿烂+且试天下已完结(三皇子×十一娘,白风息×袁慎)5.卿卿日常已完结(郝葭篇)6.点燃我温暖你已完结(大明星x大导演)cp李峋7.浮图缘已完结(肖铎×荣安皇后)8.少年歌行已完结(后宫文cp无心/萧瑟/雷无桀/苏暮雨/无双/唐莲/白发仙/白王/李凡松)9.狂飙已完结(cp安欣/李响/高启盛/高启强)10.重紫已完结(后宫文cp洛音凡/楚不复/秦珂/亡月/慕玉/卓昊/文紫)11星落凝成糖已完结(后宫文cp少典有琴/帝岚绝/清衡/顶云/嘲风/乌玳)12黑暗荣耀已完结(后宫文cp全在俊/河道英/周汝正/文东恩。)13.爱情而已已完结(CP宋三川)14.长月烬明热更中(后宫文cp澹台烬/萧凛/叶清宇)
- 120.0万字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