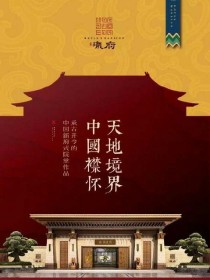基督的曙光(1)
早期的教会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组织。基督教徒一旦看清世界末日还很遥远,最后审判日也不会随着耶稣之死立即降临,基督教徒还会在被泪水浸泡的尘世中度过漫漫时光,便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或多或少比较定形的管理体制。
最早的基督教徒是在犹太教会堂中集会的,因为那时的信徒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出现了裂痕,非犹太人就到某个人的家中集会,如果找不到足够大的房间来容纳全部虔诚的信徒(还有好奇者),他们就在露天或者废弃的采石场上集会。
起初,这种集会都在安息日举行,但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和非犹太人基督教徒之间的矛盾日增,非犹太基督教徒便放弃了以星期六为安息日的习惯,将集会改在星期日,也就是死者的复活日。
这些仪式虽然庄重,却体现了整个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大众化和感情化的特色。集会时,没有固定的演讲或说教,也没有说教者,不论男人女人,只要感受到圣火的激励,随时都可以站起来证实自己的内心信仰。如果我们相信保罗信函的话,这些虔诚的兄弟们直抒胸臆的话语,常常使这位伟大使徒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因为教徒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百姓,尽管这些即兴演说中所包含的真诚不容怀疑,但是他们的情绪常常会过于激动,像是些躁狂症病人的呓语。教会虽然不怕迫害,但是对于冷嘲热讽却无能为力。于是,保罗和彼得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以使这种精神宣泄和对宗教神灵的热情变得有序一些,而不是使之处于混乱状态。
这些努力起初收效甚微,因为固定的仪式貌似与基督教信仰的民主精神大相径庭。不过呢,实际的考虑最终占了上风,集会开始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集会开始时,他们先朗读一段赞美诗(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人基督教徒)。然后教众就会齐唱一曲为罗马和希腊信徒新近谱写的颂歌。
唯一预先确定的致词是一段包含了耶稣全部人生哲学的著名祷文。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讲道从来都是完全自发的,谁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就会登台讲道。
集会的人数和次数渐渐增多,一直都对秘密团体心怀戒备的警察开始进行盘查了。这时必须选出某些人来代表基督教徒同外界打交道。保罗早就高度赞扬过领导的才能。他曾把自己在亚洲和希腊见到的众多小教会们比作船只,这些船只在汹涌的风浪中颠簸,要想不被大海的狂涛吞没,船上必须有一个聪敏的舵手。
就这样,信徒们再次集会,选出了男女执事。执事由虔诚的信徒担任,他们是教会的“仆人”,负责照料病者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教徒非常关心的大事),并且负责管理教会的财产,料理其他一切日常事务。
再后来,随着教会成员数量的持续增多,管理工作变得越来越繁杂,必须有专职人员才可以胜任,因此便把这些工作委托给一小撮“长者”负责。这些人在希腊语中被称为“长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士”。
又过了若干年,每个城镇、村庄都有了自己的基督教教堂,因此又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政策。这时又选出了“监督”(或主教)来监督全区的教务,并指导教区与罗马政府之间的交涉事务。
很快,在罗马帝国的各个主要城镇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主教都被人们当做声名显赫的权威人物,其重要性与其行省中的军政长官不相上下。
在开始阶段,掌管耶路撒冷的主教自然备受人们尊敬,因为耶稣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最后又在这里受难死去。但是在耶路撒冷圣城被毁,期待世界末日来临和天国胜利的那一代人从地球上绝迹之后,那位可怜的老主教眼看着自己失去了之前的声望。
自然而然地,这个教众领袖的位置被罗马主教取代了,主教居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里,护卫着保罗和彼得这两位伟大的西方使徒殉道的地方。
这位主教和其他主教一样,被人称为“教父”或者“神父”,这是对神职人员表达敬爱之意的一种通用的称谓。然而在几百年间,在人们心目中“神父”这个头衔逐渐成了罗马主教专用的名词。当人们说起“主教”的时候,指的就是罗马主教,而绝不是君士坦丁堡主教或者迦太基主教。这完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就像今天我们读报纸时遇见“总统”的字眼,不必再加上“美国”几个字来加以限定一样。我们知道,那指的是政府的首脑,而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或哈佛大学校长或国际联盟主席。
“主教”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里,是在公元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权力在皇权的笼罩之下显得暗淡无光,但是在此后的300年中,由于内忧外患的不断威胁,恺撒的继任者们开始寻找一处更安全的新住所。他们在自己国土的另一处找到了一座名为拜占庭的城市。该城名来自于一位神话英雄,他叫拜扎斯,据说特洛伊战争之后不久,拜扎斯曾在此登陆。该城坐落于分割欧洲和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着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商贸通路,而且还掌握着好几处重要的垄断都会。由于其在商业上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斯巴达和雅典曾为了争夺这座富饶的要塞而大动干戈。
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拜占庭一直是独立的。成为马其顿的领土之后没过多久,它又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如今,历经千年的持续繁荣,其有“金号角”美誉的海港里泊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为罗马帝国的首都。
留在罗马的人落入了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蛮族手里。帝国的皇宫数年空无一人,政府机构一个接一个地搬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当罗马首都的居民要听命于约1609千米之外的人制定的法律时,这些人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都是此长彼消。随着皇帝的出走,留下来的主教就成了城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皇位之荣耀的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继承者。
于是,这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被主教们利用到了极致。由于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全意大利的精英,这些主教们也都是些精明的政治家。他们觉得自己是某种永恒信念的代表,所以他们不慌不忙,而总是以一种冰河消融般的迟缓来渐进,在机会到来时大胆抓住。他们不像别的人急于求成而草率行事,继而忙中出错,最终落得前功尽弃。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认定一个目标,且坚持不懈地朝着那一个目标前进的人。他们的所做所想所说,都受到一种愿望的指引,这种愿望就是为上帝增光以及使代表神意的教会组织更加强大。
他们的工作效果如何,此后1000年的历史自有论述。
其他的城邦都在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的洪流中消失殆尽,帝国的城墙一段接一段地倒塌,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上那样古老的上千体制被像垃圾一样扫除干净,只有基督教一直巍然屹立着,坚如磐石,尤其是在中世纪。
不过,最终获取的这一胜利,却付出了非常惊人的代价。
基督教起源于马厩据《新约》福音书记载,圣母玛利亚在马厩中生下了耶稣。,最终却得以登堂入室。它最初是对宗教强制形式的一种抗议——在那种宗教桎梏中,教士自命为神与人之间的媒介,要求所有的凡夫俗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这一力求革命的新团体发展成一个超级神权集团,与之相比,原先的犹太国倒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幸福宁静的自由之邦。
然而,所有这一切均完全符合逻辑又几乎不可避免的,我即刻对这一点作出说明。
到罗马游览的人大都会去参观圆形剧场科利西姆,在那早已风化的围墙里,人们会看到一个大坑,在那里,曾经有数千位基督教徒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尽管对基督教徒有过好几次迫害,但这与宗教专制却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迫害完全是政治性的。
作为众多宗教派别之一,基督教曾经享有极大的自由。但是有些基督教徒公然声称自己是和平主义信仰者,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威胁时仍然大肆鼓吹反战论,不顾场合地公开蔑视本国的土地法,这样的基督教徒自然被当做国家的敌人,受到相应的处决。
基督教徒按照自己最为神圣的信念行事,但一般的治安官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教徒试图解释其道德精神的确切本质,这些长官大人们却满脸迷惘,完全弄不懂教徒们在说什么。
罗马的治安官终究都是普通人。当他们突然被叫去审讯犯人,却发现犯人的供述不过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自然摸不着头脑。长期的经验教会了他们,要远离形形色色的神学争论。更何况,许多皇家敕令也对这些公务员们加以警告:对付新教派时,一定要运用一些“手段”。所以他们就圆通地与对方理论。但是当全部争论最终都集中到原则问题时,逻辑的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最终,长官大人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无理地坚持执行国家的最高权力?然而,对于那些坚信死亡是新生之始的基督教徒来说,监禁和酷刑并没什么可怕的。当听到获准离开这个悲惨世界前往天堂时,他们还欢呼雀跃呢!
就这样,基督教徒和当局之间终于爆发了漫长而痛苦的游击战。究竟有多少人伤亡,我们没有掌握到准确的数字。依照公元3世纪著名神父奥利金奥利金(约185—254):希腊教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好几位亲属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宗教迫害中被杀的说法,“为信仰而死的真正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可以很容易地统计出来。”
我们追究一下早期圣徒的生平踪迹,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系列的血腥故事。我们禁不住心生疑惑:一个如此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何以能流传下来呢?
不论我给出什么数字,肯定都会有人说我是个带有偏见的骗子,所以我将保留观念,而由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人们只要研读一下罗马皇帝德西厄斯(249—251年在位)和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的生平,自然会对那段最黑暗的迫害时期的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有一个相当清楚的认知。
此外,如果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如此开明的君主都承认:不能很好地处理基督教徒的问题,就会明白远在帝国的偏僻角落,又想尽忠职守的无名小吏们所面临的难题了:他们必须或者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言,或者处决自己的邻居亲朋,因为这些人不能或者不愿遵守帝国政府赖以自保的几条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教徒们并没有因为异教徒的虚伪温情而止步,而是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公元4世纪晚期,罗马元老院中的基督教徒抱怨说,聚在一个异教偶像的阴影下使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于是,格拉提恩皇帝便下令将胜利女神像搬走了。这座女神像在恺撒修建的大厅内已经矗立了400多年。好几位元老对此举提出异议,结果非但毫无益处,而且还导致其中的一些人被发配流放。
这时,有一位声名远播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勒留?希马丘斯,写了一封有名的信,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为什么我们这些异教徒和基督教邻居不能平静和谐地相处呢?我们抬起头望到的是同样的星空,我们是并肩走在同一行星上的伙伴,而且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人们选择不同的道路追寻终极真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生命的奥秘如此费解,通向答案的途径不该只有一条。”
这样想的人不止一个,也有不止一个人看到罗马宗教宽容的传统已经受到威胁。就在胜利女神像被搬移的时候,罗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双方是拜占庭的两派相互对立的基督教徒。这次争吵引发了有史以来关于宽容的一场最富智慧的讨论。讨论的负责人是哲学家泰米斯提厄斯,这个人一直信奉祖先的神灵,当瓦伦斯皇帝在正统基督教徒和非正统基督教徒的争论中偏袒一方时,泰米斯提厄斯觉得有责任提醒皇帝不要忘了自己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这么一个王国,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在其中施展任何权威。这就是道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其中实行强制,势必会导致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皈依和伪善。所以统治者还是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凭借宽容才能避免民众的争吵与冲突。何况宽容还是一道神圣的道义。上帝自己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只有上帝才能判断人类渴望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正确与否。上帝在对他奉献的各种崇拜中感到高兴,他喜欢基督教徒使用的某种典仪方式,也喜欢希腊人、埃及人的其他典仪方式。”
这说得多好,可惜却是对牛弹琴。
旧的世界及其观念和理想一起死去,任何让历史时钟倒转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则意味着磨难。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迅速地瓦解,军队全是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反叛暴徒,边境地区已经处于公开叛乱的状态,英格兰等边远地区则早已屈从于野蛮民族公元410年,罗马放弃了不列颠,将其占领军撤出,其后不久,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了不列颠。手下。
当大灾难终于降临时,几百年来一直投身政界的聪明的年轻人发现,所有晋升之阶都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教会任职。如果你是西班牙主教,就可以行使先前由地方长官执掌的权力;如果你是基督教作家,只要愿意全身心地投入神学命题,就一定可以拥有众多读者;如果你是基督教外交官,只要肯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代表罗马主教,或者敢于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的腹心地带,与那些野蛮部落的酋长修好,就一定能够迅速飞黄腾达;如果你是基督教财务官,则可以通过管理那些迅速扩大的房地产来发财致富,就像拉特兰宫的占有者一样,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富豪。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也目睹了一些具有相同性质的事情。到1914年为止,欧洲中部那些野心勃勃、不依靠手工劳动谋生的年轻人,几乎悉数进入了国家机构。他们在不同的帝国陆军、皇家海军里担任军官;他们占据着司法机构的高级职位,掌管财政,或者在殖民地担任几年地方长官或驻军司令。他们并不期待变得非常富有,但是职位给他们带来极高的社会声望,而且只要再发挥一些智慧、勤奋和诚实,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舒适而又备受尊敬的晚年。
宽容(美国历史学家,亨德利克威廉房龙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黄巢揭竿传奇
- 50.6万字2年前
- 记鱼汤史
- 简介:在无尽的MC大陆上,鱼汤之国的历史
- 0.4万字2年前
- 使命召唤14:二战
- 简介:一个令几千万人丧命的战争,一场为了和平的战争,终于在1939年9月1日打响......而一个生在和平年代19岁的美国少年却无意间回到了二战,感受到了.......战争的残忍……吧?
- 1.6万字2年前
- 上下5000年那些事
- 简介:一起谈天说地,聊聊这5000年那些事
- 2.8万字2年前
- 柏林城南措森下
- 简介:1945年,我,乌尔里希•林茵斯特成为措森郊区防守长官。仓促应战前,我何去何从?该如何摆脱被监禁的命运?这是我必须思考的问题,投降,是不可能了,但如何凭借手下四千人不到的729师完成一次次的作战任务,活下来……
- 4.6万字1年前
- 大秦:历史答题
- 简介:这人很懒,啥都没写。
- 0.2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