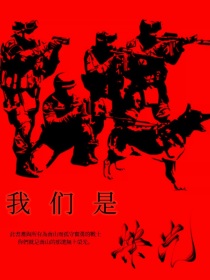宗教审判庭(2)
但是不论怎样牵强附会,这些也构不成公开叛乱的罪名。只是偶尔有人建议教士可以像普通教民一样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有人拒绝在领主出战时跟随参战(哦,想想那些可怜的古代殉教者吧!);有人想学一点拉丁文,以便可以自己阅读和研究福音书;有人表示不赞成死刑;有人否认存在炼狱,尽管基督死后600年,它就被官方正式宣布为基督教天国的一部分;而且还有人拒绝把自己收入的1/10缴纳给教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细节)指“什一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6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利用《圣经》中的“农牧产品1/10属于上帝”的说法,向居民征收什一税,教会法上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779年查理大帝也规定,缴纳什一税是法兰克王国每个居民的义务。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西欧各国才陆续废除,英国一直征收到1936年。。
教会总要尽可能查出这些叛逆活动的领袖们,有的时候,如果这些人不听规劝,就会被悄悄地除掉。
但是,这种邪恶继续蔓延,最后普罗旺斯的主教们不得不聚集起来召开一个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办法来制止这种非常危险的、具有高度煽动性的骚动。他们不断地召开会议,并讨论,一直延续到公元1056年。
这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一般性的惩罚和革除教籍已经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
那些一心想要过“纯净的生活”的平民百姓们,乐得能有机会在铁窗下表现基督徒的宽容忍让精神,万一被判处死刑,他们也会带着羔羊般的顺从走向火刑柱。而且,一个殉教者留下的空缺,立刻会有10个人怀着神圣的感情补上。
罗马教廷方面的代表坚持要进行更残酷的迫害,而当地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他们知道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指令,并且抗议说,暴力只会刺激异端更加深入人心,听不进任何道理,那样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双方的争执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彼得?韦尔多
11世纪后期,这场运动又从北方获得了新的动力。
在与普罗旺斯隔着罗纳河相望的里昂小镇里,住着一位名叫彼得?韦尔多的商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又极为善良宽厚的慷慨之人,一心想要效仿救世主的榜样,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
耶稣曾经教导说,一个富有的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几十代基督徒一直想弄明白耶稣说这句话的确切含义。而彼得?韦尔多却不费那种心思。他读了这句话后便对此深信不疑。他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了穷人,退出了商业,不再积累新的财富。
约翰写道:“汝等须自寻《圣经》。”
20位教皇给这句话加了评论,还审慎地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凡人才可以不需要教士的帮助,而直接研读《圣经》。
彼得?韦尔多却另有看法。
约翰说了“汝等须自寻《圣经》”。
那么好吧,彼得?韦尔多就自己读。
当他发现自己读到的东西跟圣徒杰罗姆的说法并不吻合的时候,便把《新约》译成了他自己的母语,并把他的翻译稿向普罗旺斯各地散发。
开始,他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他那种对清贫的热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大不了他会在别人的建议下建立起某种新的禁欲的修道院规章,以满足那些希望过艰苦生活,抱怨现有的修道院太奢侈、太舒适的人的需要。
罗马总是善于寻找一些合适的发泄渠道,以免那些信仰过于强烈的人惹是生非。
但是要做这种事情必须符合规定,循规蹈矩地来进行。在这方面,普罗旺斯的“纯洁的人”和里昂的“穷苦人”却犯了可怕的错误。他们不仅不向主教通报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斗胆宣称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一个人即使没有专业教士的帮助,也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还说罗马主教无权指挥他管辖之外的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强迫人们应该信奉什么,正如塔尔塔里的大公爵和巴格达的哈里发没有这种权限一样。
教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平心而论,它是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才最终下决心用武力来消除这种异端邪说的。
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基于原则认定只有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其他的方式都是不正当的,应该受到谴责与诅咒;那么,其权威性一旦受到公开质疑时,它必定会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
教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别想继续维持下去。正是这种考虑迫使罗马采取坚决的行动,炮制出一系列的惩罚措施,让所有潜在的持异见者心怀恐惧。
阿尔比教派(因阿尔比城而得名的异教徒,该城为新教义的温床)和韦尔多教派(以它的创始人彼得?韦尔多的名字命名)所在的城市没有多少政治价值,因而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于是被罗马教廷选做第一批牺牲品。
教皇的一名代表统治普罗旺斯许多年,他一直把那里当成被自己征服的土地,作威作福,结果被人杀死了。这样一起被谋杀案给了英诺森三世一个干涉的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的十字军,攻打阿尔比教派和韦尔多教派。
凡是参加讨伐异端的连续40天远征的人,可以免付所欠债务的利息,可以赦免过去和将来的罪孽,还可以暂时免受普通法庭所作的司法审判。这是相当优惠的条件,对北欧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和去东方的远征相比,攻打普罗旺斯的富裕城市能给自己带来同样的精神和经济的报偿,这种服役期短,而又能得到同等荣耀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地跑到东方的巴勒斯坦去呢?
人们暂时忘记了“圣地”,法兰西北部、英格兰南部、奥地利、撒克逊和波兰的贵族绅士中的败类们纷纷涌到南方,借以逃避地方的司法长官,准备用普罗旺斯人的财富,把自己空空的钱箱重新填满。
被这些勇敢的十字军士兵绞死、烧死、淹死、砍头、肢解的男人女人和幼童究竟有多少,莫衷一是。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遇害。在各地发生的正式的屠杀中,具体的数字都是讳莫如深的。不过,在这次事件中,根据城镇的大小,各处的死者数字应该在2000人~2万人之间。
贝济埃城被攻陷后,士兵们一时之间分辨不清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他们把这个问题交给教皇代表——他是随军作为精神顾问的。
“我的孩子们,”这位“大善人”说道,“去把他们统统杀掉好了,我主自然会知晓谁是他的顺民。”
但是在所有这些正牌的十字军中,有一位叫做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英国人,他是那位著名的德?蒙特福特的父亲。由于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杀人手段,他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作为对他“卓著功勋”的回报,他得到了在那里掠夺的大片土地,而他的部下自然也一一论功行赏。
至于从那场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韦尔多派教徒,他们最后的韦尔多教徒都逃到了人迹罕至的皮耶德蒙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地区。的山谷,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教堂,一直坚持到宗教改革时代。
阿尔比派教徒则没有这么幸运,经过一个世纪的鞭打绞杀,他们的名字从宗教裁判所的报告中消失了。但是300年后,他们的教义稍加改头换面,便再次出现了,并且被一个叫做马丁?路德的撒克逊教士大加宣扬、传播。这些教义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教廷保持了将近1500年的垄断统治。
这些当然瞒过了精明的英诺森三世那双犀利的眼眸。在他看来,难关已经渡过,绝对地服从已经被再次成功地确立起来。在《路加福音》中,耶稣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个打算举行聚会请客的人,发现他的宴会厅里还有空位,几位客人还没有来,于是他就招呼仆人:“去到大街上拉几个人进来!”——那条著名的命令再次得以实现。
“他们”,那些异端分子,就是勉强被拉进来的。
问题是怎样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待在教会里,这个问题多年以后仍未解决。
之后,经过地方法院的很多不成功试验,欧洲的各个首都纷纷建立了特别的调查法庭,就像最早在阿尔比教徒起义时建立的那种法庭。这些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各种异端案件,后来被称为“宗教法庭”。
即使在今天,宗教法庭虽然早已不复存在,提起这个名字仍然会给我们心头带来一阵莫名的不安。我们仿佛看见了哈瓦那的地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克博物馆里生锈的大铁锅和烙人的刑具,看见黄色的头帽和黑色的面具,看见一个长着巨大下巴的国王,用眼睛斜视着那队望不到尽头的男男女女,慢慢地走向绞架。
19世纪后期的几部深受欢迎的小说中,无疑都与这种阴森可怖的印象有关。即使扣掉25%作者的主观想象,再扣掉25%新教徒的偏见,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巨大的恐怖。这足以证明,所有的秘密法庭都是些让人难以忍受的恶魔,绝不应该容忍它再次出现在文明人的社会里。
亨利?查尔斯?李在论述宗教法庭时写了厚厚8卷的长篇巨著,我在这里只能把它缩减为两三页,在这样短的篇幅中,要对中世纪史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进行简明的叙述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可以和现在的最高法院或者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国家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们都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而创建的。
最臭名昭著的要数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异端裁判所。前者带有地方性,负责监视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端活动;而后者则把它的魔爪伸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在北方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方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
然而,严格地说来,宗教法庭的确没有杀过一个人。
在教士法官组成的法庭宣判以后,被定罪的异教徒罪犯就交给了世俗当局,他们可以任意决定怎样处置罪犯。但是,假如他们没有判处罪犯死刑,就有可能面临很多麻烦,很可能会被逐出教会,或者失去罗马教廷的支持。有时候罪犯会逃脱这种命运,没有被交给地方法官,那么他只会更加倒霉。因为他可能要在异端裁判所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由于死在火刑柱上要好于在黑暗的岩石城堡里慢慢被折磨到发疯,所以很多罪犯大包大揽地承认了许多自己根本没做过的事,以期被定为异端邪说罪,早日脱离终身囚禁的苦海。
谈论这个问题,要让人觉得你不偏不倚,那是不可能的。
让人发疯的折磨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50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是因为多嘴的邻居信口开河,便被人半夜三更从床上拖走;他们也许会在脏污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等到一位既不知姓名也不知道身份的法官现身;他们也不会知道自己究竟被控何罪,也不允许他们知道是谁在指控他们;他们不能和自己的家人联系,也不能咨询律师;假如他们继续辩解自己无罪,就会遭到酷刑,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教徒可以对他们进行不利的举证,却不允许被告提供任何有利于自己的证言;直到最后被处死,他们都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此厄运。
更难以想象的是,已经死去五六十年的男男女女,也会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缺席”定罪。以这种方式被判有罪的人,死后50年他们的后代还要被剥夺世俗财产。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由于宗教法庭主要靠没收的财产来维持他们的存在,所以这样的荒唐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怀疑祖辈几十年前做了什么事,就把孙辈逼得上街乞讨,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凡是读过20年前俄国沙皇权力全盛时期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密探”。通常这些密探都是些洗手不干的小偷或者赌徒,他们都比较引人注意,而且带着一副“悲伤”的样子。他会悄悄地告诉别人,不幸的经历让他自己参加了革命,这样常常能够换取到那些真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是一旦他知道了自己新朋友的秘密,就会把他们出卖给警察,口袋里装着赏金,奔赴另外一个城市去重操这一卑鄙的伎俩。
在13世纪、14世纪和15世纪,西欧和南欧到处游荡着这种穷凶极恶的密探,他们靠告发那些批评教会或者对教义中的某些观点提出疑问的人来谋生。
假如实在找不出异端分子,那就要靠这些密探人为地凭空捏造几个出来。
因为他们完全有把握,不论被捕者如何清白无辜,在酷刑之下都必定会屈打成招,所以他们不必冒任何风险,可以把这个行当继续做下去,无休无止。
在很多国家,允许人们匿名告发他人思想不端,这就在人们的头上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影。结果,没有人敢信任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就连一家人之间也不得不心怀戒意。
那些执掌着大量宗教裁判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地利用了他们这种办法造成的惊恐,依靠搜刮民脂民膏过活,几乎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大批人民群众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已经痛恨到了极点。他们披着虔诚的僧袍,随意闯进安分守己的人家里,要睡最舒服的床,吃最好的饭菜,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应该被当做贵宾对待。他们会威胁说,如果得不到自己理所应当享用的这些,就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们的施主,于是没有人敢对他们说半个不字。
对此,教会当然可以解释说,宗教法庭只是起着精神健康检察官的作用,其职责就是防止错误思想在群众中蔓延开来。它还可以指出自己对那些由于无知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是多么宽宏大量,还会说除了叛教者和屡教屡犯者以外,没有人被判处过死刑。
但是即使如此,又能怎么样呢?
同样一种手段,既可以把一个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能够使他表面上悔过自新。
密探与造假者从来是一丘之貉。
对于在奸细的行当中,几份伪造的文件又算得了什么呢?
宽容(美国历史学家,亨德利克威廉房龙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们是荣光
- 简介:我想写出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孤勇军队。只因我的朋友告诉我:大大小小的战役参加过不计其数,连续做了五六年的前线士兵,抵着铁棍勇敢前进过,高举旗帜等待支援的食物和水过,和战友们一起承受着毒气弹的痛苦过……我们什么都承受过,却连战友的脸都没有看清过。——《我们是荣光》,致敬为国家舍身而挡的战士们,你们就是至上的荣光。保持速度更新中,多夸夸就更得更快!一个会员加更1章!!
- 3.2万字2年前
- 醉唐风流
- 简介: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大唐。贞观九年病逝的太上皇李渊生龙活虎,一家子其乐融融。这时候,李二还是个在李渊底下励精图治的皇二代,长孙还是那个乖巧如一的儿媳妇。程咬金挥舞着三板斧继续当着自己的滚刀肉,长孙无忌成天掰着手指头琢磨着自家的铁器生意到底能赚多少利润。历史老师宁书成穿越而来,却没想到李二让他官居一品,长孙视他为半子,程咬金秦琼认了他当干侄子,就算是太上皇李渊也要叫他做当朝驸马。可宁书成只想率性生活,却没想一不小心横行大唐。本书数字版权由“讯读”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本书数字版权由“讯读”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联系话本客服(我的-设置-客服咨询内)。
- 107.3万字2年前
- 锦衣大明
- 简介:卧底刑警梁叛,缉毒身死后魂穿大明,成为了一名小捕快,奈何被锦衣卫看上了。他原本只想赚钱娶妻生子,踏踏实实当个富家翁,没想到却成为了大明朝的救世主!本书数字版权由“讯读”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本书数字版权由“讯读”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联系话本客服(我的-设置-客服咨询内)。
- 117.2万字2年前
- 穿越三国之我是曹安民
- 简介:一朝穿越成炮灰,逆天改命却无为
- 21.8万字2年前
- 战地:中华崛起
- 简介:由三国演义4改编而成。
- 0.7万字1年前
- 绛与苍
- 简介:标题就不说什么了,大家先去看内容吧。PS.文中的背景和科技仿照唐朝时期
- 1.4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