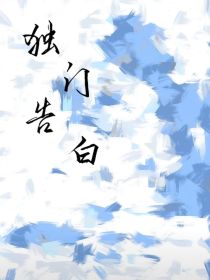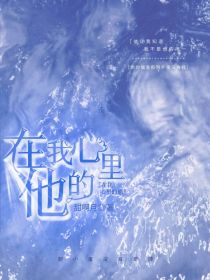9
9
夏雨终于放下一副冷漠脸开始和梁冬讲话了,他把梁冬叫到阳台上问道:“你是不是经常喝酒?”
梁冬一脸无辜的挠挠头说:“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全校都知道的事吗?”
梁冬红着脸尴尬的笑着,不知道怎么说了。
夏雨又说:“咱们说好了你不能再喝酒。”
“可以啊,不过你得答应我。”梁冬放开了一些说。
“答应你什么?”夏雨抬起头看着梁冬问。
“当然是,是,是做我女朋友咯。”梁冬又笑的一脸无赖相,倒是夏雨笑着红了脸。
“这个嘛,没那么简单,但你不戒酒是绝对不可能的。”夏雨一脸认真的说。
“好吧,看在未来女朋友的面上,我暂且戒了。”
“不是暂且,是永远。”
“这个难度也太大了,是不是条件也应该加啊?”
“你想怎么样啊?”
“我想你永远和我在一起那我就永远不喝酒。”这一下我着实佩服梁冬撩妹的功夫了,要是撩其他人估计早就成功了,偏偏要挑情窦还未开的夏雨,他简直就是自讨苦吃嘛!
“想得美,这个不太可能的。”夏雨白了他一眼说。
“为什么?”
“我不想一辈子和任何人在一起,我喜欢自由。”
“我又不妨碍你自由。”
“我说妨碍了就是妨碍了。”他们的谈话被上课铃声终止了,梁冬又看到了希望,对此他很开心,我为他开心也为自己伤心。
这次谈话之后梁冬开始步入了追女孩子的正常轨迹。第二天他起的出奇的早,我和夏雨走到教室门口时他突然跳出来,左手抬着一碗粥,右手握着两个鸡蛋,他满脸笑意的递给夏雨。夏雨不接,他有些着急了,“不接就不许进教室。”说完他张开手臂挡住了门,夏雨想要从他手臂下面钻过去,他脸上的笑意消失了,他走到垃圾桶面前回过头来说:“你不要的话我就扔了”。我一直觉得夏雨对粮食的感情都比比梁冬的感情深厚,应该说夏雨对世间万物都有深厚的感情,唯独对梁冬没有。看着好端端的早点要被糟蹋掉,夏雨着急了,她赶忙跑到垃圾桶面前从梁冬手里把粥和鸡蛋接过来,我吃还不行吗?怎么可以浪费呢?她说。梁冬的奸计得逞了,他得意的笑着,看着夏雨吃早点。我走到他面前把他的视线挡了,靠边儿去,他说。我没好气的对说:“我的呢?”——你的什么?他一脸无辜的问。我的早点啊,我说。你的早点在食堂,自己不会去打吗?——重色轻友的东西,我白了他一眼。他笑着对我眨了一下眼睛说:“帮我搞定她,来日必有重谢”。我瞪了他一眼说了一个“切”就操起碗筷独自下楼打早点去了。
梁冬本来是个非常懒惰的人,可为了给夏雨献殷勤他变得出奇的勤快,早上起来给夏雨打早点不说,晚上还要去买宵夜让人带去给夏雨。梁冬买的东西夏雨一般不吃,都分给舍友吃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对我来说得到的都是要还的,我还不起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欠下。”事实上虽然东西是我们吃的,但人情依旧是夏雨欠下的,这个道理她自己也清楚。所以作为偿还她也给梁冬买一些东西,梁冬觉得自己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他开心得不得了。
夏雨和我都非常喜欢看课外书,但我们全井底乡连一个书店都没有,学校里倒是有一间图书室,但那个图书室的门一直紧锁,图书室简直就是徒有虚名。老师们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时间花在课外书上,但说实话我觉得看课外书不是浪费时间,再说了难道不让我们看课外书我们就会学习了吗,简直就是笑话。我们宁愿去做一些违反班规校纪的事当做消遣也不愿学习,我们为啥做那么多荒唐的事啊?说到底都是闲的,都说闲愁闲愁,那么多愁都是闲出来,为了消愁啊,我们总得做点什么来打发时间。要是我们把一半的时间花在学习上,那也不会让校长看着我们不堪入目的成绩时悲伤的说:“以后别忘了回母校扫扫墓,毕竟这是埋葬你们青春和未来的地方。”
学校不开放图书室这件事让我和夏雨都非常气愤。夏雨说学校简直就是浪费资源,我连珠炮似的说这帮傻逼老师难道要把那些书留着下儿?难道他们不知道读书可以开阔眼界?咱们农村娃最缺啥?缺的就是眼界,读书啊那是咱们了解外界的唯一渠道了,可他们就这么残忍的把唯一的渠道都给断了,他们啊一点远见卓识都没有,妈的,还不如我。我说完,夏雨张着嘴呆呆的看着我,我说:“咋了?是不是听了我的高见之后有点自惭形秽了?”她点点头说还真有点儿。看着她那副傻傻的样子我不由得哈哈大笑。你笑什么啊?——你记不记得《夏洛特烦恼》里面夏洛对大春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买二环内的房子?以后亲戚都不要见了?我摇摇头,她想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了,是“你和别人不一样,你读书就是浪费时间”哈哈哈,这句话也很适合你啊。我止住了笑,真没想到她想到的居然是这一句,虽然这一句确实是适合用来形容我,但听了总感觉不大舒服。不是,是“真羡慕你像傻逼一样活着”我,羡慕你像傻逼一样活着。她看了我一会儿说:这句话不应该是我对你说吗?我想反驳回去,但又觉得好像是这样,事实胜于雄辩,我还是承认吧。
虽然我们既买不到书也借不到书,但我和夏雨还是看了不少课外书,毫不谦虚的说,这是我的功劳。我爸爸每年过年的时候回来一次,他回来的时候我总是要让他帮我买书,我知道夏雨也爱看书,所以我把我的书全部带到学校分她看,毕业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课本和练习册全卖了,只带着半口袋课外书回去。我爸买的书看完了我便要去班上收罗别人的书,看到谁桌子上有就直接拿了,我看了再给夏雨看。到最后实在没书可看了我和夏雨的课余时间全部用来趴在阳台上,有时候说几句话,有时候就只是呆呆的看着操场上的人来人往。梁冬也发现了我们两个这个习惯,于是下了十分钟他都要运着篮球往球场上跑。为了在夏雨面前表现自己啊,他可没少下苦功夫,一招一式都像提前设计好的,他在球场上简直就是如鱼得水,引得球场上经过的人驻足观望,和我们一样趴在阳台上的女生欢呼雀跃。我不知道夏雨到底有没有在看他,她啊永远是这样,让人猜不透她的心思。
梁冬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的篮球表演并没有夏雨对他的态度有多大改变,倒是有其他的女生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下晚自习之后有两个一班的女生来我们宿舍门口说是找夏雨,夏雨出去了,宿舍门是开着的,我听到了她们之间的对话。那个高一点的女生轻蔑的说:“你就是夏雨啊?”夏雨点点头说是。矮一点的女生一脸不屑的说:“也不怎么样嘛!我还以为长得花容月貌呢!”说完那两个女生相视一笑。我看她们完全就是来找茬的,上一次夏雨挨了一巴掌就因为我胆小,不敢帮她,虽然我帮她了也顶多是我也挨一巴掌,不过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不能退缩了,这么想着我出去站在了夏雨旁边。夏雨看了我一眼又面不改色的问那两个女生有事吗。高一点的女生说:“梁冬是我的,你离他远点。”——哟,是你的啊?把你倒贴一百万送给他他也未必要啊。说出这么一句话,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但夏雨瞪了我一眼,我马上把笑容收了,摆出一副假正经的样子。矮一点那个女生说:“你谁啊?没跟你说话你插什么嘴?”——我谁,我不就是夏雨和梁冬的朋友咯!——原来是第三者啊!她们两个奸诈的笑了。你他妈的才是第三者呢!我没好气的吼了回去。要打架啊你?她们两个被我激怒了。打就打谁怕谁?——别吵了,夏雨突然发声。他是你的我不会跟你争,你们走吧!——你就认怂啦?梁冬也太没眼光了。她们两个无耻的笑了。那你们想怎么样?夏雨问。想怎么样?就是想打一架。——我不喜欢打架——怕了?——怕你爹哦,我的暴脾气终于克制不住了。不怕更好,周五放学之后在学校背后的小路上等你,不来的是孙子。说完她们两个走了。等她们两个下楼了夏雨没好气的跟我说:“都怪你,你这暴脾气能不能收一收。”——还不是为了你。听她这么说我很生气。算了算了,我不跟你吵。说完她无可奈何的上床去了,那表情大有觉得我不可救药之意。那是一个周三的晚上,周四一整天我们两个都没有讲话。
周五上午的课间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夏雨趴在阳台上发青春呆。我在座位上装模作样的看那本看了好几遍的《小王子》。夏雨走到我旁边呆呆的站着,看着我看书。她看得我很不自在,干嘛?我问。她突然从背后拿出一根棒棒糖递给我,一脸赔笑的对我说:你终于跟我讲话了。我把棒棒糖撕开放到嘴里说:谁跟你讲话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行吧,我大人不记小人过,下不为例啊。——咱们下午去还是不去?——当然去啊!——我没有打过架哎!——说的像谁打过似的。小学的时候有个男生调戏我,我把他打哭了,但和同性我还真没有打过架。这么想着我也有些犹豫了。但不去的话岂不是很没面子?我说等我想想。
最后我和夏雨还是去了,活着嘛总得感受一下各种各样的人生,好学生也应该感受一下坏学生的生活。我一直不喜欢太单纯的人,因为太单纯的人往往太单调。我想这也是我喜欢和夏雨待在一起的原因,虽然她的外表很乖巧,其实她的内心很疯狂。
我们去的时候那两个女生已经等在那里了,直接打架未免也太突兀太鲁莽了,所以打架之前需要一阵出口成脏的对骂来渲染气氛,奠定基调,等双方都面红耳赤了再顺理成章的扭打在一起。我和高那个女生对打,夏雨对付矮的那个。我费尽千辛万苦才把那个女生压到了地上,正准备好好的赏她几巴掌,回过头来看夏雨却被那个又胖又矮的女生按翻了。我连忙跑过去一把把那个胖女生推翻到一边,把夏雨拉起来,那个高的女生一脚踢到了我大腿上,把我疼得直骂娘。我猛扑过去给了她一大巴掌,扇得我手掌都疼了。她尖叫这过来扯我的头发,我终于发现女生打架和男生打架的区别了——男生用脚踢,用拳头打,女生则擅长扯头发,扇巴掌或者用手指掐。这场恶战持续了接近一个小时,我们都累得精疲力尽,她们两个坐在一边,我和夏雨坐在一边,各自喘着粗气。妈的,老子以后再找你们两个算账。说着她们两个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走了。也不怎么样吗?我还以为很能打呢!我笑着看看夏雨。我们学校里总有这么一些人明明不怎么样,偏偏要摆出一副大佬的样子去恐吓那些比较乖的人,她们以为夏雨和其他好学生一样乖,好学生是不敢打架,可惜她们失算了,谁让夏雨有我这么一个朋友呢?我为自己感到骄傲,也为夏雨感到骄傲。
我和夏雨身上都敷了一层黄土,夏雨的衣服被扯破了,一块布挂在胸前飘。我们两个面对面坐着,我觉得她的样子很滑稽,她也觉得我的样子滑稽,我们两个就一个笑一个,笑得前俯后仰,笑得眼泪都流出来,笑的实在累了才停住了笑声。她摸摸脸上被抓伤的地方说:这副样子怎么回家去啊?——去我家啊——好吧!我们两个拍拍身上的灰,背起书包顺着小路走了。
到我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大雾罩了上来,潮湿的空气给我们的头发挂上了串串水珠。到村口时我们遇到了骑在马背上赶着羊群的归来的刘老爹。他甩着鞭子对我说:“小谣谣,咋才回来啊!”我说了一个“嗯”算作是回答。走了几步有又遇到几个背着猪草的女人。老王头的媳妇儿对我说:丫头啊,你会想你爹妈不?——一点都不想,我不耐烦的说。走远了我还听到她们几个议论说;“这丫头真可怜,爹妈都不在身边,就一个人过日子。”我最讨厌那些一脸同情的揭别人伤疤的人,他们那么做时一定以为自己是无比善良的,而他们之所以满目悲戚想必是被自己的善良感动坏了。
到了家门口我拿出钥匙开了门,屋里是我习惯了的冷冷清清。我开了灯,放下书包,然后从门口抱来几块柴,把火给点着了。你先烤着火,我去买点菜——好。说完我就出门去了。村口的老邓家的儿子是开着面包车卖菜的,他家里也卖一些零食。我进他家大门的时候那条大黑狗疯狂的向我汪汪着。我拿了一坨花菜和两包辣条,付钱的时候发现还差着两块,我说:先赊着吧——谣谣啊,你上次买的也是赊着的——那就再赊一次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提着东西出门时说。
我回去的时候夏雨已经煮了饭。打开辣条让她吃着我就去洗花菜了,水很冰,把手冻得生疼,但我太饿了已经等不得烧热水来洗菜了。把菜洗好之后夏雨炒菜,我吃辣条。虽然只有一个菜,但可能是太饿了,也可能是因为夏雨厨艺比较好,我们两个都吃的很多。吃了饭之后我找出针线给她缝衣服,她笑着说: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贤妻良母的一面。——你看不出来的事多了,我说。她东张西望的看着我家被火烟熏得漆黑的土墙。是不是觉得很寒碜?我缝着衣服问她。没,我家也是一样的。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很认真的盯着我问:“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那你为什么要学习呢?——因为,我穷怕了。她抬头望着瓦片接着说:小学的时候我每天放学都要去背猪草,你别看我个子高,可我根本就没有力气,我堂妹个子还比我小,可人家就是能背一大筐猪草。我背回去的猪草不够,我爸爸就骂我是废物。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我就换用我妈背的大筐去背,我把猪草装满了,却怎么也背不起来,我使劲的背啊,可是箩筐才离地我又被压得坐到了地上。我试着起了好多次之后终于背起来了,东倒西歪的走了几步就从地埂上摔下来了。她擦了擦眼泪,吸了吸鼻涕又接着说:一大筐猪草压在我手上,我手脱臼了。我妈一边骂我一边射着手电筒带我去找隔壁村的刘医生看手。她射着手电筒走在前面,嘴里不停地骂着,她说:嫁到你们夏家真是老子倒了八辈子的霉了,你那个爹不成器,生的娃娃也不成器,要不是有你们就一走了之了……骂着骂着她就哭了,我也哭,可是我不敢哭出声来。他们说我笨也说我什么事都干不好,我知道他们也是被生活逼急了,说到底都是因为穷,所以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走出去。我递了一卷纸给她。不知不觉自己的眼泪也掉了下来。其实不是我的生活不苦,只是我一直在逃避思考,逃避回忆,逃避现实,因为这些东西会让我觉得痛苦,所以我总是用一副傻逼的样子面对别人。用林语堂的话说: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欢幽默的,这是寂寞的内心的安全瓣。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她抹干了眼泪说。我真不愿意有人真正了解我,我可不希望别人觉得我楚楚可怜。但看着她期待的眼神,我还是说了。我啊,其实好像过得挺好的,不缺吃不缺穿,就是有点缺爱。我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学习,因为我觉得学习需要理由,不学习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学校里大部分人都是不学习的。我妈跑了,我爸去打工了,我奶奶死了以后我就一个人住,我觉得根本没有人会在意我,只有我犯错了才会引起别人的一点点注意,我就是不想学,毕业以后我就出去打工,那时候我再也不用依靠任何人了,我用自己挣的钱,那不是挺好的吗?——你就想一辈子做个打工妹吗?——我没有你那么大的抱负,我只想有个自己的家,有个爱我的人,我就很满足了。——可是老师不是说好好学习以后才能过得轻松点吗?——那些不识字的不也有当大老板的啊,老师都说了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但老师说那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最容易走的路了。——你好好读书就行,还是别管我了,我是自由惯了的人。——好吧,人各有志。她低下了头不说话了。
周六是一个阴天,这时候已经入冬了,一旦没了太阳天气就很冷。如果在百度上输入我家乡的地名便会出现:该地海拔2300-2800m,年平均温度8度,属于“凉山”地区,这里物产单一,荞麦和土豆是主要的农作物,这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其它的信息也许对夏雨有用,但对我是没用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年均温8度。在这里夏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要穿着保暖裤,到了冬天就更了不得了。天这么冷,衣服怎么办?——别洗了,穿我的。——那头发呢?——也别洗了。——我上周就没洗了。——我上周也没洗啊!管它的,要是洗感冒了怎么办?还是活命要紧。那时候我们那里的大多数人家还连吹风机也没有,我家也没有,要洗头只能挑晴天,不然头发会结冰的,就算不结冰也要把人冻得够呛。
周天起来门口已经一片雪白了,下了雪反倒感觉没有那么冷了。我们去上学的的路是很难走的。春秋季节,在庄稼还没有发芽或者已经被收割了的时候,路上的泥土是松软细腻的,就像面粉一样,被风一吹便铺天盖地的来了,打在脸上,那些灰尘努力的钻进脸上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毛孔,到了学校基本成了一个“泥娃娃”,脸上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土色的“粉底”,擤出来鼻涕也成了泥浆,衣服一抖便是一阵黄灰。有时候运气不太好,一进学校就遇到那些班上的小混混,他们嬉皮笑脸的对我说:“你这是从泥巴堆里钻出来的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一言不合就摔碗的暴脾气,我没好气的对他们说:“你全家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夏天的时候若是天气晴朗,便是烈日当空,每每晒得汗流浃背、头晕目眩,若是雨天就像第一次去学校一样,下半身基本都是湿的,鞋子和裤腿上敷满了那些所谓扶不上墙的烂泥,到了学校脱了鞋袜,脚底泛白,皮肤被泡软了,一撕就能撕下一大块,有的时候还会惹上蚂蟥,那便又要牺牲点血添一个疤了。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放牛的男孩子赤身裸体的在路边的河里洗澡,他们一看到我和夏雨就无耻的笑着喊:小姑娘,来洗澡啊,很舒服的。夏雨红着脸低着头走得很快,我就吼那些男生:放你爹的五香麻辣屁,你爹没告诉你男女有别吗?。他们倒不生气,依旧笑着说:姑娘脾气这么大啊,男女有什么区别啊?要不你脱了我们比比看。我捡起一个石头扔进水塘里,溅得他们一脸的水,扔完石头我拉着夏雨跑了。
然而最难走的还是冬天,从我家到学校要走很长一段下坡路,当大地银装素裹时那段下坡路就成了一块天然的滑冰场,当然,它可不像滑冰场那么简单,这路是很逼仄的,弯弯曲曲的,沟沟坎坎的,忽陡忽缓的。夏雨和我要一起上了这段坡才分路,所以常常一起回家,要去学校的的时候我们就在路口汇合。我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所以下坡的时候我基本是滑下去的,偶尔也会摔跤。夏雨这种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就基本是连滚带爬下去的。因为下雪走路要更费时间,所以夏雨我们两个起来炒了一点饭吃了就出发了。
还没到那段下坡路呢,夏雨已经摔了一跤。我拉着你走吧,说着我伸出了手。她的手很小也很冰,被我握了一会儿就暖暖的了。下坡路开始了,我们走得小心翼翼,她好几次差点摔倒都被我拉住了,但有一处很陡也很滑,她滑了一下把我也带倒了,她跪着我坐着,我们两个一起滑了很远。滑下去的时候她的膝盖撞到了石头,我拉她起来,她的脚一跛一跛的,她红着眼睛笑着看着我。我看着她,一不小心又摔了一跤。她的脸被毛叶蔷薇的刺划出了两道血口子,我的胳膊肘撞出了一大块淤青,当皮肤冰冷的时候疼痛尤其的清晰。这样的痛会让我感到痛快,我想痛快就是痛而畅快的意思,但太痛了还是难以忍受的。我坐在地上大喊:老子不想读书了,于是群山也悲怆而愤怒地回应我一句:老子不想读书了。群山的模仿让我很生气,我又吼它们:你不读书关老子屁事。群山也吼我:你不读书关老子屁事。这太让我伤心了,没想到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却对我如此无情。夏雨说:我好想哭啊——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我吼道。说完夏雨嚎啕大哭起来,我仰面朝天躺在雪地上等她哭完。她的哭声持续了好一会儿才渐渐变成呜咽,又过了好一会儿呜咽也停止了。走吧,她说。哭够了吗?——哭够了,真他妈的痛快。她说着就破涕为笑了。哭够了好,我拉起她接着下坡。
下了第一节晚自习,梁冬问夏雨:你脸上怎么了?——摔的,夏雨说。过了一会儿梁冬又问我:夏雨脸上的伤怎么回事?——摔的啊——怎么会摔出血口子?——下坡的时候摔了被刺刮的。——哦。我不知道梁冬在想什么,那个晚自习他都心事重重的样子。
其实一周的时间是很快的,转眼间又到了周五。周五下午上两节课就放学了,最后一节是英语课。英语老师让我们提前做一部分练习,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做,她把一根竹棍放到第一排,没做作业的自己打手,一页没做三棍子,说完她表情严肃的站到了讲台上。英语老师不喜欢打人也不喜欢骂人,她不打是因为她要让我们自己打自己,她不骂,因为她的一个眼神就可以杀人。我们都是很自觉的,主要是英雄都是敢作敢当的,我们崇拜英雄,所以我们也要敢作敢当,于是全班就只有我和夏雨一个人没有站起来打手,夏雨是做了,我是抄她的,而且是她提醒我抄的。梁冬也起来了,他右手拿着棍子打在左手上,也真下得了手,他坐下来之后一直盯着自己的通红左手看。虽然上课的气氛异常的紧张,虽然回家的路山高水长,虽然那个所谓的家也只是徒有虚名,但我仍然强烈地期盼着放学。在学校就是要受到束缚的,等待放学就是在等待解脱。我知道所有同学也都和我一样迫切的期待着下课铃声,期待着如子弹一般的冲出教室门。好不容易等到下课铃声响了,隔壁的班级已经喧闹起来,我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立不安,英语老师还在慢悠悠的布置着作业,我觉得她是有意折磨我们,我恨不得把她的语速加快十倍。
英语老师终于提着书走出来了教室,这次梁冬一马当先的冲了出去。我也拉着夏雨跑向宿舍,我们飞快的收拾好衣服,到学校门口买了一点在路上吃的零食就上路了。我们走过了街道,快到大路和小路的分叉路口时我突然看到了梁冬,他骑在摩托上,正望着我们这边。干嘛你?——我送你们回去。我有些惊讶,没想到他这么有心。我们走近了,上车吧,他得意洋洋的说。夏雨却说:谢谢你,但是不用了,我们自己会回去的。说着就往小路走,梁冬把摩托骑到她面前堵住了她的去路,你什么意思啊?梁冬问。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自己会回去。夏雨走了两步,梁冬又把摩托骑过去了,梁冬向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上车,我骑了上去说:夏雨上来吧,又不要车费。——民谣,你下来。——你上来。我们僵持了好半天夏雨终于上车了。我让她坐我前面,可她非要坐我后面。
今天虽然没有下雪,但还罩着雾,空气湿漉漉的还刮着冷风,依旧非常冷。摩托走起来风就更大了,不一会儿我全身都凉透了,夏雨抱着我,把头放在我背上,我听到了她不停的吸鼻涕。梁冬耳朵冻得通红,他在前面把大部分风都给挡住了,他冷得抖起来,但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用力的抱紧梁冬,希望这样他会暖和一点。摩托沿着盘山公路爬升,海拔越来越高,气温越来越低,我们头上都结满了霜,我问梁冬冷不冷啊,他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还行吧!我也和梁冬一起送夏雨到她们村的村口,下车时我们三个的头发上都白了。她下车后对梁冬的态度缓和了一些。要不去我家烤烤火吃点饭再走吧!她对梁冬说。有你这句话就够了,但还是不去了,我还得回去呢!——你呢?去我家吗?夏雨转向了我。——我?还是不去了吧!——走吧,上周我去你家,刚好这周我去你家。反正我那个家也确实没意思,我下了车跟她去了。
到她家时已经是傍晚了,大雾淹没了她的村庄,天色黑沉沉的盖下来。我们刚回去的时候只有她九十多岁的老祖一个人在家,她在拨弄着火煮猪食,那火烧得很旺,火舌不停地往灶们外窜,猪食已经冒出了白气。
夏雨指着我对她老祖说:老祖,这个是我同学。她老祖回过头看了看我们,你同学啊,她点了点头慈祥的笑着说。夏雨又接着问:我妈他们呢?——他们去挖洋芋了。夏明呢?这是她的弟弟,我曾听她说过。——他放学回来就去放羊了,夏丽呢?这是她的妹妹,她也跟我提过。——她去扯猪草了。这像是一场仪式性的对话,估计是每次回家都会这么问的,一场对话之后就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她的家人们在天色即将全部黑下来时几乎同时回来了。先进门的是她母亲,她的母亲个子高高的,脸上长着一些雀斑,不太笑,看上去不太容易亲近。然后是她的父亲,个子不高头发有些微微的卷曲。之后她的妹妹背着满满一筐猪草回来了,她的妹妹眼睛很大,看到有生人就显得有些害羞。最后进来的是他的弟弟,有十岁左右吧。手里还拿着羊鞭,脚上穿着的黑色水靴,水靴上敷满了厚厚的泥浆,呼哈呼哈的吸着鼻涕,估计是让初冬的寒意侵袭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皮肤黝黑,不过也不算特点,这个地区的不都是黝黑的么?只不过他们的黝黑更有深度罢了。
夏雨介绍到:这是我同学。她父母的反应和她老祖差不多,只是她的弟弟妹妹还有些拘谨,倒像是他们到我家做客而不是我去他们家做客。她的母亲问到:你煮饭了吗?——饭煮了,菜还没整。听完她的母亲就拿起菜刀去屋里割了一块腊肉。我知道他们今晚本来应该是不准备吃肉的,但农村的大人们总是认为有客人来时不可不吃肉,所以不管把腊肉有多难洗,当有客人来时都必须准备。他们已经劳累一天了,我不想他们为我而再辛苦一次,而且对我来说吃不吃肉倒也不是那么重要。我说:嬢嬢,你不要麻烦了。不麻烦的,她说。
农村的大人总是这样,一切事情都默默地去做,却没有太多的言语表达。于是作为农村孩子的我们也是自从能够走稳就永远的失去了在父母面前撒娇取宠的机会。我们与父母之间有很远的距离,不是代沟,不是不能互相理解,只是谁都不善于表达,谁都羞于表达。
我们农村父母与孩子之间不会有什么表达,这我是知道的。但我发现他们家的人说话尤其的少,他们家的屋里尤其的安静,特别是她的父母之间几乎就没有交流。明明一大家子人却总有一种冷冷清清的感觉,弄得我也有些局促不安,无所适从。
吃饭的时候夏雨的母亲一直给我夹菜,她的父亲呢拿出了酒,说是请我喝酒。她母亲瞪了她父亲一大眼说:人家一个小姑娘,喝什么酒。你那个马尿实在好喝了,少喝一顿会死吗?不过我还是接了酒杯,我会喝酒让他很高兴,如同找到了知己。楼板上有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夏雨的父亲说:这是一个大耗子,要不我去打了煮给你们吃。我笑了,她的父亲真幽默。我们吃完了饭,可夏雨父亲的酒杯依旧放在他面前,他时不时就要抬起来喝一口。也不知道喝了多少,他站起来打开碗柜门,夏雨的母亲问他要做什么,他说他要上厕所。他“上完厕所”回来之后就唱起了山歌:喊声姑娘你听我说,你和夏雨是同学,你们之间处朋友啊,坦诚相待包容着……那一晚他的山歌唱到半夜。到最后他甚至哭哭啼啼的唱起了孝歌——一对白鹤飞过河,口中含着三颗药。问你白鹤飞什么,有人病了来送药。一对白鹤飞过江,口中含着三柱香。问你白鹤飞什么,亡人死了来烧香……
第二天吃完早饭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又出工了,夏雨没有出工,因为要留在家里洗一周以来家里存下的所有脏衣服。她的老祖撩起裤脚,在遍布老年斑的小腿上搓着麻线,口里念念有词,不知道说些什么。我对夏雨说:其实你们家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嘛。——也许吧,一个人是否感到痛苦不在于痛苦本身的严重程度,而在于一个人对痛苦的感知程度。——好深奥哦,能说的通俗易懂点?——这就像我以前看到过一句话——一个人思想是否成熟不在于他的实际年龄而是他思想矛盾的结果。——所以呢?——所以不同的人对同样的生活产生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也许别人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天经地义,但我不觉得。——为什么?——也许我更敏感吧!——那我就是不敏感的人咯。——不敏感也许更好。——为什么?——可以少一点痛苦。——可你这么说着我突然觉得不敏感就是不懂事。——嗯~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吧!夏雨的这席话让我思考了好久,最后我觉得这种深奥的问题实在不适合我也就放弃思考了。
自由疯长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四面包围
- 0.3万字2年前
- 独门告白
- 简介:(作者还有一百天会考正在做最后的冲刺,更新时间不定)“我曾经真的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一个人,甚至都没有想过会有人喜欢……我……管他江渝安是不是男生,我一定要和他一直在一起。”“他啊,他这个人,幼稚,顽固,有的时候矛盾的很,但是,他很好,没有人比他更好了。”“虽然我不理解两个男生怎么会在一起,不过作为你的朋友,我会站在你这边,支持你们。”“爸爸妈妈那,你们就别担心了,我去跟他们说,世上的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快乐的不是吗,他们不会为难你们的。”“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啊?”“……我也爱你。”
- 0.5万字2年前
- 全能大佬掉马甲中
- 简介:“如花美眷,也敌不过流年似水———流年似水·书店”[已于2020.9.28签约][该书为上册,已完结,下册在团宠更新][原创,禁止抄袭转载二原创,只发布在话本,若在外站出现,必定维权走法律程序!]冰山女神白梓汐对上高冷直男林隽辰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白梓汐——白家不受宠的“叛逆”大小姐,逃课打架,“无恶不作”,名声扫地,一朝到了一中,结识了林隽辰等人,马甲数数被扒,开启甜甜恋爱之路。………………部分剧透:白梓汐在电脑桌前飞速编辑着一条信息,身后一人放了一杯温牛奶在她身侧,“乖,喝了睡觉”白梓汐抬眼看他,“不喝,你先去睡吧”林隽辰盯着她的背影,双手环着她撑在桌沿上,把人圈在怀里,他把头偏在白梓汐脸颊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她的脸上,溅起青春的情愫,“不喝?嗯?”,心里乱慌慌的白梓汐耳边响着男人低沉的声音,耳尖微微发红,脸色也红润起来,“别闹”男人下巴抵在她肩膀上,“我没闹...”男人磁性的声音微微带些撒娇的意味白梓汐:……………………林隽辰刚刚忙完,开了门便躺在沙发上小憩,白梓汐瞥了他一眼,默默从房间里抱了床被子出来给他搭上,“真是的,也不怕着凉”给他盖好了被子,白梓汐起身要离开,大脑已经放空的林隽辰伸手拉住了她的手腕,冰凉的触感在手腕处刺激她的神经,“有你在,我不怕”身后的男人目光炽热的望着她的背影,笑道。………………[宠文,双洁,无脑打脸,女强]不喜勿进!!!!
- 46.5万字2年前
- 转身拥抱阳光
- 简介:“我叫苏晴,晴天的晴”。正是她如一缕阳光,照进了白枫心里,治愈了他,也给自己一份甜甜的小确幸
- 1.0万字2年前
- 校草大人腹黑宠
- 简介:软萌可爱的女主江星甜在一次意外中竟然将高冷校草顾子晨扑倒强吻了!从那以后,江星甜苦哈哈的看着眼前的李柯泽,心里郁闷的大喊:“说好的高冷校草呢,我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假的呀!”
- 0.3万字2年前
- 在我心里的他
- 简介:年少时的心动是我青春的证明,那些藏在我心里的秘密都需要被知晓。在骄阳正好的日子里,它们陪我享清风明月,在阴暗无日的时光里,它们为我扛下风雨。我的喜欢叫做暗恋,这是我一个人的腥风血雨,是我最年少的秘密。
- 0.6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