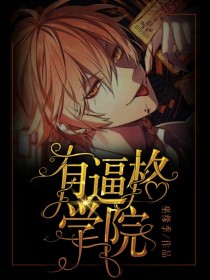【虞美人草】摘录(五)
自世界与自世界发生抵牾,有人会切腹,有人会自戕;自世界与他世界抵牾,则会导致两个世界会同时崩溃,它们爆裂开来随处飞散,或一声巨响之后拖着滚烫的尾气消失于无极。一生中只要发生一次如此激烈的抵牾,人就不必站上闭幕舞台,照样亦能成为悲剧的主人公,受赐于天的本性此时方始表现为第一义。在八点发出的夜车上交集的两个世界当然不会如此激烈,然而,如果只是相遇又离别的萍聚缘分,他们也就没有交集的必然——在星影深沉的春夜,在连名称都带着苍凉味道的七条街道。小说可以摹状自然,自然本身却无法成为小说。
两个世界不即不离、如梦幻似的在绵延二百里的火车旅程中交集。至于这二百里的旅程载牛还是载马,抑或将何人的命运如何搬运至东方,火车根本漠不关心。火车只是隆隆滚动着不畏这世界的铁轮,在黑暗中勇往直前。乘客中有归心似箭的离人,有别情依依的恋人,有快意四海的旅人,但火车统统等而视之,仿佛对待一堆陶土人偶一般。暗夜中伸手不见五指,唯有火车不知疲倦地喷吐着黑烟。
紫色招骄矜者蜂攒,黄色引深情者追求。二百里铁路连接东西两地之春,心愿的细丝犹如发髻上纸发绳扎成的平元结,颤颤袅袅,祈祷着真诚之爱,在长夜中一路往前奔驰。往昔五年是一场梦。饱蘸颜料的绘笔淋漓尽致泼染出的往昔之梦,已深深浸透了记忆,每每回首拾取当时记忆,颜色依然鲜明如新。
火车载着梦一个劲地向东行。怀揣美梦的人为了不让美梦失落,紧紧搂住腾升不熄之物向东行。火车专心致志向前猛冲,冲过平野的草木,冲过山间的云雾,冲过夜空的群星向前疾驰。心怀梦想的人愈往前行,鲜明的梦想便愈远离黑暗,渐渐呈现于现实世界面前。随着火车的疾驰,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愈加接近。
人的过去模糊到连人狗草木都无法辨识时,才会真正成为过去,人愈是留恋无情抛弃我们的往昔,往昔的人狗草木便显得愈加杂乱无章。
火车刺破层层围裹的黑夜,掀翻竭力阻遏的逆风,车尾猛力捶打穷追不舍的黑夜之神,终于冲出黑暗国,迎向白晓国的缕缕霄霞。奇怪呀,茫茫原野怎么会无休无止地不停向上升腾逼向天空?挥却残梦睁大眼睛扫向半空时,日轮已经照亮世界。
神话时代啸鸣不止的金鸡振翅五百里,盎溢的仙云便随之纷披而下,太虚中扬浮起万古晴雪,以威压八州之势渐次向四面八方倾泻,整个苍莽大地自腰部以下都被埋入白茫茫之中。白雪逞炫似地充贯天空。白雪流泻一阵后,裂成数条不规则的白练,斜斜地被覆于紫色蓝色的襞褶之上。抬眼眺览的人顺着在大地攀延的云影,从山脚的苍茫原野望向仿佛被雷电刺破的紫色蓝色皱褶,直至顶端的一片纯白,会情不自禁豁然惊醒。白雪吸引了明亮世界中的所有乘客。
散装书摘与文摘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帮助广大网友解决作文难题
- 简介:帮助广大网友解决作文难题
- 0.3万字2年前
- 下潜到海底
- 0.4万字2年前
- 茶久封面铺
- 简介:【绿色话本围绕我,加我拿图】封面:根据下单日期,章节自取,找不到加下方联系方式。【下单+找图+上传】步骤,见评论区置顶。店铺封面,不溶图不修图,对底图有要求,后台自己提供底图,留言看不见的。非美工做错【书名/笔名】,一律不改图。【更多注意事项,见评论区本人置顶。】建设绿色和谐话本,拒绝污言秽语口吐芬芳。
- 15.2万字2年前
- 有逼格学院
- 简介:无,最近有删改建议从头看
- 1.5万字2年前
- 星辰天衍
- 简介:这人很懒,啥都没写。
- 2.9万字2年前
- 雪梦:执笔绘丹青
- 简介:【雪梦】:雪楼凝芬芳,梦里花飘落【本书于2021.6.30在本网站签约】【本书禁止随意ky翻墙辱骂等行为】本书为雪梦文社独创,版权归雪梦文社所有,禁止抄袭借鉴效仿剧情。本书客串已满,请勿加报。————————————————“听说了吗,江湖上人人都畏惧的雪梦组织原来是一大群女子!”“别说是女子,个个手段高明,出手敏捷,文采兼备啊!”“知道么,她们这个组织有一个共同的代号——黑玫瑰。”——————————————“黑玫瑰象征着神秘与高贵,同时也是死亡的代表。”——南宫凝雪“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一定要留给自己。”——上官雨馨“我的狙击枪下不留活口,只因为我是一位合格的狙击手。”——予落“我优秀的身手是我用汗水和泪水浇灌而成的。”——蒋云昕“轻视对手的人,一定会付出代价。要知道在这场博弈里,没有弱者。”——江茹绫“危险永远都没有过去,永远都是刚刚开始的。”——洛初柠“能留下来的都是最好的。”——伊莫“我只想做那个在暗处的帮者,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柚橘“在这一行里能活下来的就没有简单的人”——蝶扇姬“没有什么是天生的,不要抱怨也不要烦,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沐玛“曲线救国只是无稽之谈,七十六号只不过是一个屏障罢了。”——顾语钗“一个人如果是无端的让人产生怀疑,哪怕是没有证据一定也是有问题。”——顾妍钗————————————————本书执笔者:雪梦文社社长:江茹绫雪梦文社QQ群:1034315586同系列书:1.《雪梦:一任群芳妒》作者:雪梦文社社长:Snow_南宫凝雪2.《雪梦:虚梦代价》作者:雪梦活跃部长:Snow_上官雨馨3.《雪梦:时代的游戏》作者:雪梦灵感部长:Snow_蒋云昕4.《雪梦穿越第五:决裁者》作者:雪梦文编部成员:snow_叶昔辞5.《雪梦:凭酒寄红颜》作者:雪梦文编部成员:snow_洛初柠另:特地感谢封面制作:五维虚空-江邱璟
- 6.3万字2年前